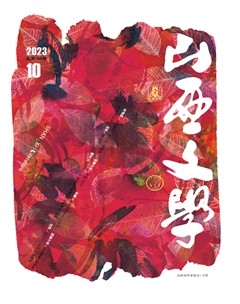老领导老作家孙思义(义夫)离开我们,已经一月有余,但是自己仍然无法从因病未能在他生前再去探望一面的缺憾当中摆脱出来。回想自1984年底进入运城市文联工作近四十年来与孙主任相处相知的点点滴滴,更是千头万绪、乱麻一般不知从何处忆起。电子版的稿子不知道点开过多少次,记写下多少内容,总难顺畅成文,一直凌乱在文档里面。时值刊物要组织编发纪念特辑,只好把诸多片段连缀起来,权作哀思之寄托吧。
虚惊一场
我是1984年岁末进的运城市文联,二十来岁,年龄最小,北京知青背景的司机师傅陈潞纯正京腔的一句“小李子”,全单位人便约定俗成地管我叫小李了。那时候,大家都把李逸民主席称作主任,几位副主席也一样称主任。其中的第一副主席就是孙主任,因为不久就在他亲自签名赠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1984年短篇小说选》里读到他的作品《花花牛》,他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品印在文学作品集里面的作家本人,这也是自己获赠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一时间,孙主任在我眼目当中,就成了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当时单位是在运城地区报社隔壁原来文化局视导组所在的地方办公,就是横竖几排砖瓦平房,而且是与教育局儀器站、招生办、拼音报社印刷厂几个单位在一个大院里面,它们都各自形成独立空间,只有文联的大办公室所在的排房面临公共通道。办公室三通间带一个套间,里外全是一人多高黄色木制带门书柜。置身其中,有一种进了图书馆的感觉。而它们,都归我保管,如果把柜门都打开,露出里面一排排的文学作品,取一本坐在办公桌前翻开来,真有坐拥书城般惬意与富有的陶醉感觉。而我,就住在套间里面一张靠后墙根的木床上,头顶的是书柜,脚蹬的还是书柜。
有一天拿着写的稿子给孙主任看,他的意见,要注意写生活,小说可不是空编哩。他又说起《花花牛》里面的人物,都是从他熟悉的农村乡亲们身上集中提炼典型出来的。他又指着办公室一圈的书柜说,里面好作品太多哩,你先好好读,看名家们咋写。记得他还说过,从事文学写作,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爱好、天才、生活、技巧。
自己非常庆幸选对了单位,能这么零距离聆听、领教知名作家的指导、教诲,太荣幸了。当时就发愿,一定要读完所有书柜里面的文学作品,以期成为像李主任、孙主任还有王自强(草章)、张毅二位主编那样的作家。
如此,白天除了干好办公室的工作,有时间就记写自己构思的小说;夜里更是按照《中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简编》大学教程讲授的作品顺序,一本本读着文学名著,国内的和国外的作品交替进行。常常折腾到很晚,甚至是天快亮,星期六夜里更是会放开读到天大亮了,才伸伸懒腰倒头昏昏睡去。
一直忘不了冬天的一个早上,都上班了,孙主任见大办公室的门还没有开,就隔着窗户朝套间里面喊我的名字,见没有动静,就敲打玻璃窗框,还是不见动静,他着急的迅疾撕扯开外面的窗纱,用力推开窗扇,朝着仍然沉浸梦中的自己大声喊叫,并准备跳窗户而入,因为他怕我中了煤气。那时候,办公室外间和里间各生了一个铁炉子烧钢炭取暖。看着里间办公桌上摊的书本,孙主任问,多会才睡的?我迷迷糊糊说,天快亮了吧。他说天不亮我到大门口上厕所的时候,就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你在里头么。看书还能看那么晚?
我不好意思地说越读越不瞌睡,就……他笑着说:叫你读,也要慢慢来,馍馍要一口口吃,盖厦要一砖一砖垒,罗马城敢是一黑夜就能建成的?
背地里推荐《丢丢》上了《火花》
对孙主任作品的认识,就始于他的《花花牛》。作品风趣幽默的叙述风格,常令自己读得忍俊不禁,陶醉其中,从而让一门心思要当写小说的作家、却又处于被不同作家风格迥异的小说作品搞得眼花缭乱、不得要领而盲目乱写状态的自己,获得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启发,现在说来,就是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眼,见到了光亮。
全国著名老作家、陕西作协副主席王汶石,是孙主任的万荣老乡,一直关注家乡的文学创作。记得当时他读到孙主任这篇山西文学获奖作品,特地写了一封信,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中肯地提出缺点与不足。孙主任把这封评论性质的信投递给《山西日报》发表了。许多作家朋友读到后表示:义夫在作品获奖的一片喝彩声中,还愿意把带有批评意见的信公开发表,这就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勇气,说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而对于初学写作的自己而言,可谓是多了一个认识这篇优秀作品的角度,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些被指出来的不足与缺点呢?这样的解剖麻雀现身说法式的学习效果,真是非常有效地提高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认识,更是促进了自己写作的积极性。随后,自己就以在解州五龙峪乡和后来在永济郭李乡新街村两次扶贫下乡积累下的鲜活素材,创作出短篇小说《丢丢》,发在了1991年《河东文学》第六期上,这是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等刊物印出来后的某一天,孙主任特意上到三楼的宿舍里,和我说这篇小说写得有生活,人物很幽默(他发音为mei),应该能发到省刊上的。他还第一次肯定我能写小说。就这么好好写,几篇就写出来啦。这个鼓励,太重要了,我像打了兴奋剂,脑子似乎也更加灵光起来,脑子里的素材越发多了起来,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又写出了《丑女》和《曲曲》。前一篇也在《河东文学》上刊发了,后一篇,当时主编觉得触及“文革”,又是以植棉模范曲耀离为原型,不好把握,就没有刊用。
转过年的一天,孙主任拿着一本省文联办的文艺期刊 《火花》送给我,说有我的作品。深感意外的自己迫不及待地翻开目录,就看见目录页第二面“新作评介”栏目上,单独推出了我的小说《丢丢》,还配有一篇题为《风趣 幽默 形象化》的评论,作者王培民。我问孙主任这位评论老师是谁,我也没有给《火花》投稿呀?
孙主任这才说,本来应该推荐给《山西文学》,听我说已经退了稿,所以就写信连同那一期《河东文学》邮寄给《火花》的老编辑王培民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刊用,所以就没有告诉我。这也太突然了,一种得到期待的认可的幸福感,搞得本来就笨嘴拙舌的自己更是语无伦次,无以名状!
回头主要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读王老师评论。他于开头就说明了这个情由,而这个提纲挈领的题目,就说明自己这篇作品,不正是下意识模仿孙主任《花花牛》及其他相关作品语言及人物性格描写风格的学习之作吗?这是自己的作品第一次登上省级文艺期刊,还被专题评论,那种获得认可的鼓励作用,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