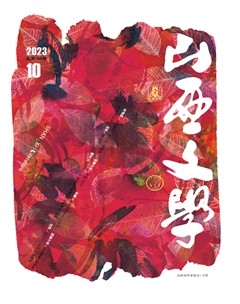大同作家陈年的中篇小说《归家》,不出预料荣获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这个奖项对她的创作是一种充分的肯定,是她十几年坚持小说写作应有的收益,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文学创作实力。
陈年小说创作的价值
《归家》讲述的故事是:因为战乱,兄妹失散;随着年岁渐老,相互思念之情更为强烈,于是,几十年后在亲属及相关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一趟充满戏剧性的寻亲之旅。客观地看,这部作品题材并不是特别新颖,类似的故事许多作家都写过;主题也没有显得多么宏大,不过是通过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变迁,说明历史与现实的不可割裂。然而,陈年却能够把如此一般性题材挖掘出新意来,把不够宏大的主题提升了意义,使得小说的内涵蕴意深刻,人物性格鲜明,故事结构富于创新,语言文字朴素,建构的艺术世界足够丰富。
陈年在获奖后写的创作谈《归去来兮》文章中说:“这个小说的时间线前后有八十年的时间,这么大的跨度,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写,必定情节拖沓,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我用了双线索,一条是以舅姥爷回乡为线索,现实和回忆交织展开,既有当年王家的生活片段,也有战场的兄弟情生死故事。另一条是由苏红来讲述,采用的是第三视角,由她来讲姥姥家各个人物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两条线,可是他们的讲述在一些事件上、人物和时间上会有交集,而且两条线相交以后,又沿着各自的轨迹往下延伸。”可见,她为了写这部作品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重点是在故事结构和叙述方式上,做足文章,显示新意,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理解空间。具体到我这个读者,从《归家》中能够读出的意义是广泛的:战场上的惨烈,战友之间的真情,苦难中的相助,老年人的个性,亲戚间的争议,等等,陈年把这些意义细腻道来,试图厘清复杂生活中的秩序、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作品呈现了看似普通的人生中蕴藏着的可贵品质,浸透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品格,富有显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陈年作为山西新世纪以来的一位有实力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上成绩斐然,无论评论界对她的文学创作能力评价是否到位,还是外界对她不少作品的理解是否准确,她都平和接受,一直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判断写作,有时会集中推出一批作品,产生集束效应;有时也会调整一段,不多发表新作。事实上,陈年的中短篇小说,在山西近二十年女作家队伍中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作者之一,在蒋韵、葛水平、张雅茜、东黎、孙频、小岸、蒋殊、陈亚珍、李燕蓉、李心丽、陈年、指尖、王芳等人组成的队伍中,由于陈年的存在,让这个群体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的山西女作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作家方阵”,撑起了山西作家队伍半边天。她们所写的题材涉及乡村、都市、过去、现在,她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女性为中心,包括社会焦点、历史事件、人文情怀、个人经历、家庭婚姻;她们的作品既充满地域特色,更是整个中国女性生存方式现状与进程的记载;她们的笔触生动细腻,叙述讲究情韵,艺术共性与个性追求合理融合,做到了跟国内外文学创作走向同步。这中间,陈年自然是尽了自己的力量,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对于山西女性创作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不少评论家和大学教师的关注,正在做专题研究,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深度分析总结的理论成果问世。
总体上评价陈年的文学道路和小说艺术特点,我个人认为,她的代表性作品大多数都能够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独特的女性视角、独特的挖掘人物情感方式、独特的结构故事手法,描写出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女性人物的心灵世界,写得真实可信,写得入木三分,写得让人共鸣。陈年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作品中是个性鲜明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普遍意义。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一直试图要摆脱男人的掌控,要主宰自己的人生命运,要体现自身的价值,要追求共同的幸福生活;她们尝试以各种方式奋斗、抗争,少数人成功突围了,而多数人的结果并不如愿;于是,她们就总是认为男性太强势,社会不公平。其实,我个人理解,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分析,是女性自己的许多性格特征造成的。外在的因素固然是男性的强势,传统力量的重压,但女性自身内在的弱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基本理念是,做个好女人的标准就是相夫教子,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抗争;而且,她们总是相信所谓命运的安排,并不认为顺从男人、忍辱负重有什么不对。陈年的小说就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以真切的视角,剖析女性的這些弱点,讲述女性的悲情故事,描写女性适应时代发展发生的变化,试图唤醒女性的抗争意识,提示男性要尊重女性的地位与能力,因此,她的小说就显得颇有价值,能够说明许多社会问题、性别问题、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是几十年来女性问题的文学化呈现。
前期的陈年小说
陈年写小说已经好多年了,我从她的一些创作谈文章中了解到,她是在一次偶然机会闯进文学这个行当中的。三十年前,一个名叫“十里河”的大同矿区文学社,让还是青春年代的陈年,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文学社走出去的知名作家夏榆,是她的启蒙老师,也是榜样。在文友们的鼓励下,陈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先是写诗歌;不久,转为小说创作。由于她的生活经验,主要是在大同煤矿系统,对那个特殊的产业环境感受特别深刻,尤其是她所接触的煤矿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众多的矿工家属,这些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的情感方式、这些人的为人处世性格,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中,所以,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让她来书写。从陈年早期小说中,我们读到的大多是黑色的煤窑矿井,朴实无华却又有点狡黠幽默的矿工,在矸石山上穿着破旧衣服、说话粗声大气、做着拣炭拾煤笨活却与矿工息息相关的女人,无拘无束疯玩生长的孩子们,以及到处是煤尘的坑坑洼洼街道和人们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这就是曾经的煤矿底层生活状态,是那一代煤矿人的真切写照。
陈年在一篇创作谈文章中坦言,曾经的一段时期,在矿区,喜爱文学并且还要写作,那可是少见的事情,人们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你。那里的男人多是以挖煤为生的重苦力高危劳动者,那里的女人多是只会干家务活的矿工家属,男人和女人的普遍性就是读书少,知道书本价值和意义的人也不多。那是通常被一些社会学者划分为“底层”的现实存在,因此,在矿区如果你是一名文学写作者,想要轻易找到志向相同的朋友,讨论文学的价值,寻找作品的意义,可能会被人视为异类。然而,不擅长交际却有主意、性格外柔内刚、没有读过大学科班的陈年,就是想要做这样的“异类”,她在完成应当做的工作和家务后,剩余时间对各种时尚活动都产生不了兴趣,却发现自己对文字有一种特殊感觉,喜欢上阅读文学作品,这样的方式,让她不必去应付与人交往时的勉强。时间一长,陈年自然地把写小说当作自己的一种生命寄托;同时,她也开始反思自己未来的人生路: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体现自己的价值?她经过认真思考,最终,感觉写小说或许是一条行得通的路。于是,凭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自己的判断,她几年时间就写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她出手不凡,凭借素材的真实和流畅的语言文字,让文学编辑认可了她的作品,于是,她的文学之路从大同矿区走向了全市,走向了山西省,多家省级刊物对她小说予以肯定,不断推出;之后,又一步一步走向省外,让她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了信心。
陈年前期小说作品题材,跟她自己的生存感受密切相关,表现的大多是底层女性的艰难困境,揭示出的基本上是人生悲剧;不过,相比于其他生活在大都市的写作女性生活的作家,她的主题立意更为平民化,更有现实感,更具典型性;或许她那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客观上,她的小说社会现实意义却是深刻的;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绝大多数是最基层的老百姓,社会阅历简单,没有多少宏大的志向,说话办事更是直截了当,自然而然性格就不太复杂;她讲述的故事情节,从不刻意追求悬念频发、离奇曲折、惊天动地,主要是注重展示小人物的生活方式,率真简单,很少使用复杂手段;至于内心世界的剖析,只是偶一为之,因为她知道,硬要给生活简单的人物赋予复杂的心态,显然是不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