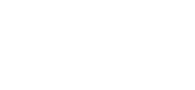一
下午两点半,几座黑矿山似的云团快速飘移过来,大得看不见边缘。等到徐青青透过大玻璃墙往外看的时候,赶路的黑矿山好似抵达了目的地,把全身重量都卸了下来,实打实砸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整个天空被拉下全幅遮光窗帘。黑矿山山体躁动不安,有泥石流快速涌动。忽然,暗黑的山体中间被生生劈开,一条闪闪发光的银蛇跳出来,随即传来某种盛大喜庆般的隆隆巨响。
候机厅玩手机聊天吃零食的全都吓了一跳,被按下暂停键,纷纷扭头朝外张望。尽管徐青青目睹了乌云迁徙,还是被它带来的电闪雷鸣惊着了,她放下手机,缓缓神儿,朝跑道上张望料想中的雨。刚才还像下雨前燕子们在湖面上穿梭低掠的飞机,这会儿也都待在地面上不动了。眼前体积最大、翅膀都看不完整的这架——徐青青略带新鲜地仔细看过,似乎靠着登机廊桥想来躲雨,但也未能幸免,全身立马被淋个湿透。
三天前,头儿把徐青青叫到办公室,面带微笑:“小徐,你坐过飞机没有?”
徐青青毫无准备,下意识答:“没有。”
头儿笑了笑:“有个公差,坐飞机,广州,准备让你去。”
徐青青没反应过来。
头儿看着徐青青说:“简单准备一下,就这两三天,听通知随时走。”随后又交代了几句此行的具体工作。
带上头儿办公室的门,喜悦才猛地涌上来,流遍徐青青的周身,像喝了有后劲儿的酒。酒劲儿沉淀下去,是一阵轻微的紧张。
下班回到家,徐青青马上为入职三年来的第一次坐飞机出差收拾起来,身份证、工作证、充电器、耳机、小化妆包,依次装进一只小箱子,又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王安忆散文》,最后仍没忘把宝贝自拍杆塞进去。刚收拾完,徐青青就迫不及待地在手机上搜广州景点,“小蛮腰”、沙面岛、珠江、上下九步行街……看着就兴奋,不过随后,她又叹了口气。
徐青青听从老爸建议,从大三上学期就着手准备公务员考试,那时她所在大学经济学院的同学大部分都眼光向上地盯着券商、基金和几家大银行。而徐青青老爸让她报考公务员的理由是:家里就你一个女孩子,做公务员稳定,还能守在爸妈身边。再者,一本学生不比名校生,还是脚踏实地的好。寝室里恰巧有学姐留下来的公考书,徐青青非常有心地把书收了起来,有空就抱着看。对文科生徐青青来说,行政能力测试里最难的就是数量关系和判断推理,照着答案勉强能理解,可自己一做题,看见复杂的图形和符号就头晕,没办法,只有大量刷题,外加碰运气。
大四上学期,气氛忽然收紧了,那些平日里打游戏吃大排档撸串的男生和谈恋爱逛街看电影的女生,突然都变回了真正的学生。曾经那些只向上看的学生也明白过来了,忙着给导师写自荐信发邮件,抢占图书馆最好的位置,一头扎进考研题,像只鸵鸟一样只露个后背示人。徐青青也受了影响,觉得研究生学历更高,将来前途肯定更好。老爸回复她:“闺女,研究生不读到博士不搞研究的话,好多还是要进体制内。况且,投行、券商、基金这些地方看着挣钱,其实压力大得很,年龄一大不吃香了还得再找出路,得不偿失。你考个对口的公务员,照样能发挥你的专业优势。”徐青青是个听人劝的孩子,老爸这么一说,她就心无旁骛了,临近考试参加了一个公考强化辅导班,一举在家乡封阳市上岸。
候机厅里传来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的播报,起飞时间待定,请乘客等候通知。声音轻柔温婉,语速和缓,春风般灌进耳朵,简直如采耳,能消解一切焦躁不安的情绪。果然,乘客们骚动了一阵,很快恢复正常,像半夜醒来,翻个身又睡着了。徐青青第一次坐飞机的新鲜劲意外地被拉长了。她无所事事,本想把书抽出来看,又觉得看不进去,顺手把耳机掏出来插进手机孔,从音频里点开莫文蔚的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把音量调到舒服的位置。一瞬间,莫文蔚湿润性感的嗓音伴着雨声,流了进来。徐青青扭头望向远处,雨幕匀实,充沛,没有尽头;停机坪安静,空旷,苍茫一片。这时,耳机里传来“终于我和你,在这里相遇,也许你就是我,未竟的心愿……”
五点十分,广播里终于传来郑州飞往广州的航班登机通知。徐青青跟随人流,顺着廊桥走向机腹,在入口处礼貌地回了空姐一句“你好”,拉着小箱子进了机舱。她打眼看看,中间过道两侧座位跟大巴车差不多。走到一个靠过道的座位,徐青青确认一下机票,就是它了,可惜不靠舷窗。刚坐下来,左脚就被人踩了一下,徐青青忙把脚收回来,抬头看见一个拉丝烫头的女人正在踮着脚放行李。女人下意识“哎呦”一声,随即扭头看向徐青青,抱歉地笑笑,鲜艳的红嘴唇把鼻子眼睛都夺走了。放好行李,女人朝里边指了指,示意要进去。徐青青收了腿,女人的黑色超短裙在她眼前短暂挡住了视线,平移过去,像舞台剧缓缓拉开幕布。
五点半,晚点了两个多小时的飞机终于起飞了。徐青青在空姐的提示下系好安全带,身体被固定后要把自己交给一段未知让她略感紧张。候机厅慢慢后退,飞机缓步滑行,正对跑道后开始提速,很快便像疯牛一样突然拉满狂奔。徐青青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是和一群人被綁在战车上义无反顾地冲锋,瞬间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机身大幅度倾斜,舷窗外乾坤失衡,腾空的徐青青立马没了着落,感觉大巴车马上就要翻,她不由屏住了呼吸。等到机身终于找到平衡,窗外跟舞台布景似的,忽然就飘浮着大块的云朵。徐青青忙扭头看向舷窗外,欣喜起来。
“徐青青?”一个男声传过来。
飞机上竟然有人叫出了自己名字,徐青青忙把目光从云彩上收回来,只见紧挨过道另一侧座位的年轻男人正看着自己:“童尧?”
“真巧啊,在飞机上碰见你!”童尧面带微笑。
徐青青礼貌地回应:“嗯嗯,真巧啊。”
短暂的沉默后,童尧说:“好快,转眼毕业三年多了,你怎么样?”
“嗯嗯,还好。你也都顺利吧?”
“还行吧,瞎忙。”童尧说。
徐青青冲童尧微笑了一下,两人随后聊了几句学校的事,就没太多话题了。
童尧很帅。瘦长脸,高鼻梁窄鼻翼,配上两道水平的浓眉,有股韓式潮男味儿。上学那会儿,童尧在资源与环境学院,与徐青青的交集是因为两人都加入了学校的播音社团,就是到校广播台播音。只不过徐青青负责播新闻,早间和午间档,童尧负责文艺栏目,俩人平时在同一微信群里听台长安排工作,只在社团例会或聚餐时遇到过几回。
这会儿,徐青青后排的一个小伙子问超短裙女人到广州怎么住,女人有些不耐烦,压低声音敷衍了一句,便不再理他。
飞机在平流层安静飞行,把厚厚的云层压在身下,好像滚在一床还没缝好的棉被上。云卷云舒,形态各异,好像仙境。徐青青一边看一边小声“哇塞”,忍不住拿起手机,往舷窗方向探了一点儿身子,变换焦距拍了个过瘾。
七点多时,广播里传来了飞机即将降落广州白云机场的播报。静息的乘客们被广播声叫醒,慢慢动起来。童尧扭过头,见徐青青正在收拾背包,随口问她:“老同学,是来广州出差还是旅游?”
徐青青说:“散散心,算是旅游吧。你呢?”
童尧“嗯”了一声:“我是来……出差。”
两人都没再问下去。
飞机缓慢下降,云层变得稀薄,丝丝缕缕,似有似无。夕阳虽已西下,但天光依然明亮。即将降下夜幕的广州,“小蛮腰”已被点亮,紧身镂空衣展露着她独有的曲线,脚下的珠江是她的T台,夜夜都是新秀场。徐青青仿佛看到,在穿梭不息的人流里,在售票处或登塔口,在旱地拔葱直达云霄的电梯里,抑或在空中旋转餐厅里,她一转脸,会与童尧再次相遇,彼此说声“这么巧。”可转念一想,童尧是来出差的,大概率不会刚到目的地就出来闲逛,而自己此行,也十分匆忙。想到这儿,徐青青笑了笑,她知道那是在笑自己。
飞机降落停稳后,乘客们开始收拾行李。徐青青站起来刚想伸手,童尧就顺手把她的那只小箱子取了下来。徐青青忙说:“谢谢。”
童尧笑笑:“同学还这么客气。”
前座的一位小姑娘背好背包,对超短裙女人说:“姐,我的脚前几天碰了,走不快,万一跟不上,等会儿我们在哪儿见?”
女人回她:“出站口吧,在那儿见面。”
收拾好行李,童尧扭过脸对徐青青说:“那就先这样了,老同学再见。”
徐青青左手举到脸旁边,五根手指同时摇一摇,小声对童尧说:“嗯嗯,拜拜。”
跟随人流,徐青青拉着小箱子到了出站口,四处眺望一番,吸了几口南国的新鲜空气。乘客不停地从出站口走出,像渔民把一网成百上千条鱼倒进船舱。趁着天没黑,徐青青背对出站口,把手机装在自拍杆上,轻点“录像”开关,一只手举起来,另一只手做个“V”的手势:“广州,我来啦!”
事实上,徐青青根本没时间去“小蛮腰”,按照头儿的安排,第二天她就返程了。落地新郑机场后她坐上了回封阳的城际铁路,进到市区,正赶上下班高峰期,车流缓慢向前,车灯依次点亮,联袂抵挡即将降临的夜幕。徐青青在城铁站出站口等了好一会儿才打到出租车,她跟师傅说了地址,出租车便一头扎进了移动的灯光长龙里。在城铁上时,徐青青给老妈发了微信,说今晚到家。老妈有点儿奇怪,给她发来语音:“广州那么远,你咋今天就回来了?”
徐青青说:“晚上想吃饺子了,茴香馅的。”
老妈说:“早说啊,我这就去买茴香。”
徐青青说:“妈,你别着急,这会儿路上堵车,我到家早着呢。”
车到金明街与黄河路交叉口,一个超长的左转红灯把车流截住,像拦腰斩断一头百足怪兽,后半身兀自躁动不安,不停发出低鸣。徐青青抬起头往窗外看,忽然在拐角的信阳菜馆门前看见一个打手机的男人,侧面很像童尧,她不由得心咚咚跳。等他转过身来,果然就是——他怎么今天也回来了?
二
广播台在学校东北角一幢爬满爬山虎的二层小楼里,徐青青童尧们的声音,从这里穿过一条小路、一个院子,再翻越两幢教学楼后,覆盖了整个校园。大一入学没多久,徐青青就报名参加学校的播音社团。入社是有门槛的。徐青青念了一段国际新闻稿,朗诵了一首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没两天,社团通知她入选,负责播报早间和午间新闻,内容自己选,但播出前要报社团的学长审核。有了一件学业之外喜欢的事做,就像春游时怀里还揣了一个史迪仔。
社团的破冰活动照例是聚餐,这是历届社团遗留的光荣传统。周五晚上,在学校西门外美食街的“海陆空”火锅店里,社团学长带领新入社的八九名成员围坐一圈,点了一个大型鸳鸯锅,亮闪闪的红油上堆满辣椒,溢满了欢迎新人的喜庆。学长提议大家用简短的话自我介绍。徐青青还没参加过这种场合,有点儿紧张地说了自己的名字和院系后,便把麦克交给了下一位同学。击鼓传花,花随人走。轮到最后一位男生,他不急不徐地说:“我叫童尧,童第周的童,尧舜禹的尧,来自资环学院,人文地理专业,爱好文艺,喜欢唱歌,很荣幸加入这个多才多艺的集体,相信会从学长和同学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指导。”
话音未落,学长带头鼓掌,说道:“好!大家开吃。”所有人哈哈哄笑起来。徐青青拿起筷子向前看了一眼最后发言的这位男生,他身材瘦高,五官立体,自带一点儿明星相。其间,学长主动引领话题,从中文系后边的小树林适合情侣出没,到数学系的教授娶了小他三十岁的女学生,再到食堂第四个窗口胖大妈打饭给得多,每个话题都有糖果扔进蚂蚁窝的效果。童尧跟着学长的话题,时不时插上几句,逗得身旁的同学筷子都拿不住了。徐青青基本没听说过这些事,不知道怎么搭话,不过她乐得听大家聊。学长看大家不怎么吃,随手往辣锅里连下几筷子羊肉,不停地招呼身旁的童尧等几个同学吃肉。童尧客气地说自己不吃辣,怕影响嗓子。学长呵呵一笑说道:“我是过来人,说吃辣椒坏嗓子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我这不是还在播音吗?”
那是个愉快的周末,火锅汤沸腾到最后一刻,宜人的晚风吹进房间,徐青青跟大家一起吃了个肚圆。
在那条通往广播台的小路上,播完午间新闻的徐青青碰到过童尧两三次,那应该是童尧提前去接下午班。徐青青远远看见童尧,若无其事地看向楼上的爬山虎,等童尧走到合适的距离,她自然地望向童尧打招呼,两人眼光一对,彼此几乎是同时说了声“你好”,很自然地就擦肩过去了。走到小路尽头转弯处,徐青青借机往回看了看,童尧已经消失在楼梯口,空气中似乎还留着他的脚步声。
下午四点,童尧主持的《青春音色》节目如约而至,清新温润的男声让人觉得不小心踏进了植被茂密的暖温带森林,迷路是必然。碰到曲库里没有听众点播的歌曲,童尧会先道个歉,然后请听众另点一首。有一次,他的女粉丝点播遇到曲库里没有歌,就别出心裁非要主持人唱一曲。童尧尽管有点儿意外,还是满足了听众的需求,他点开配乐,唱起了汪峰那首《怒放的生命》:“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社团的第二次聚餐已是散伙饭,大三下学期,还在老地方。彼时徐青青已经进入公考备考状态,脑子里装的都是试题,沉浸其中,人就有点儿像只呆鹅。文艺组一个男生过来给她倒啤酒,她连忙用手掌压住杯口。男生说:“啤酒不算酒,怎么也得喝点儿吧。”
童尧说:“算了,女孩子别让喝了。”
等啤酒沫从杯子里溢出来快流到桌子上时,男生们把杯子端起来,仰脖一饮而尽,几个女生啪啪鼓起掌来。大家开始谈论毕业后的去向,轮到徐青青,她实话实说。倒酒的男生说:“女孩子做公务员不错,稳定,旱涝保收。”
童尧接话:“你经济系的做啥公务员啊,出来挣大钱啊!”
徐青青冲童尧笑笑,不知道怎么接。童尧倒也直爽,他说自己一直想转专业,可惜喜欢玩,喜欢唱歌,耽误了,到现在还没想好毕业后干啥。徐青青直勾勾地看着童尧说:“你有才华,到哪里都会发光,只要有理想,总会实现的。”
徐青青所在的部门二十多个人,平时都挺忙的,有些人经常外出工作,不怎么见面。徐青青日常负责整理文字,制作报表,做一些会议记录,说忙忙一阵子,跟发疟疾一样。大学里高她好几届的师兄方昊,前些年考进来,现在已经是部门中层了,稳健干练,势头正猛。虽然方昊负责的工作跟徐青青没有交集,但毕竟是同校师兄,对她多有照顾。负责信息工作的叫陈卓,毕业于知名大学的计算机系,业务上很受领导器重。高配置的电脑,超大屏幕,办公桌上经常放一摞图表,墙上挂着黑板,略显散乱地排满了数字,掺杂一些符号,导出几个像飞机拉出来的长长尾烟似的箭头。当然,最后的位置上常常挂着一个问号。陈卓真像一个中学教师,或者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徐青青想。但与这些典型职业形象不同的是,陈卓不戴眼镜,也没有由于久坐显得湿气重,她甚至经常看见陈卓下班背着双肩背球包出去,一副羽毛球拍倒插在包里,使他看起来像一名时刻等待接收司令部命令的战地通信兵。
五十岁的常元磊,讲话中气十足,精力充沛,只是前额的头发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显而易见地标注了他的年龄。安排徐青青坐飞机出差的就是他。在徐青青看来,常元磊是那种业务型的领导,不太以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划线,他看重的是每个人的专业能力,方昊和陈卓就是例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也感觉工作起来比较轻松。
食堂的菜最近辣得有些过分,凡菜必有辣椒出没,红的绿的,星火燎原。辣椒是主角,大肉鸡蛋香菇白菜土豆丝啥的统统是配角。跟窗口师傅反复交代后,徐青青端着几乎看不见辣椒的饭盘,在一个略显僻静的位子上坐下。刚拿起筷子,方昊就走过来在她正对面坐下,吃了两口,说:“食堂这是换了川菜师傅吧。”
徐青青笑笑:“可不是嘛,我这盘看不见辣椒,可我还是吃不下去。”
方昊冲她笑笑说:“我去给你接碗开水,涮涮吃会好点儿。”
徐青青忙说:“不用了。”她担心让别人看到不好。可看看周边,隔壁桌就有别的部门男女同事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她又觉得自己想得有点儿多了。这时,方昊已经把一小碗开水放在徐青青面前了,他自己也接了一碗。徐青青忙表示感谢。那顿饭吃得比较愉悦,起码不再辣了。
夏天的雨就像村里来的戏班子,搭台就唱,唱一出就走。雨滴打在窗玻璃上,蜡烛流泪一样滑下来,没多大会儿就流干了。徐青青没带伞,刚才还担心怎么回家,没想到快下班时雨停了。她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机,随手拨弄了几下。打开微信时,发现通讯录上挂着红圈,连忙点开,竟然是童尧从播音社团的群聊里来申请加她好友。播音社团群从四年前那顿散伙饭后就沉寂了,像长满杂草的废弃机井,一直没有动静,她怎么也没想到童尧会从荒芜之处走出来找她。
互道“你好”后,对话框短暂地停顿。
徐青青正想着怎么往下聊,童尧发过来一条信息:“请你吃饭吧,老同学。”
这么突然,徐青青毫无防备。
童尧紧接着又发来一条:“吃火锅,就当怀念我们的播音社团。”
这个理由,徐青青不好拒绝。隔一小会儿,她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过去。
第二天下班,徐青青来到单位车棚,推出自己的电动车,掸了掸车上的浮土,拧开开关,一路匀速骑了出去。轻风吹起她白色的裙摆,承载着她的心事。
火锅店的长方形招牌鲜红亮堂,像个巨型条幅,高调得近乎嚣张。刚一进门,三个服务员齐齐躬身道:“您好!”徐青青往里走几步,又有服务员停下来点头问好,搞得徐青青觉得自己跟载誉归来似的,有点儿不好意思。童尧已经在那儿等她了,两人寒暄了两句,童尧让徐青青点菜,徐青青连忙摇头,说:“你点吧,这个我不在行。”
童尧说:“那我可做主了。”
徐青青第一次单独离童尧这么近,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又快了起来,近乎生理性的,难以控制。两人的火锅吃得真跟当年社团的破冰饭似的,不过这回是童尧不停地往辣鍋里下羊肉,招呼徐青青吃。
徐青青回忆起来说:“你不是不吃辣椒吗,不怕坏嗓子了?”
童尧笑笑说:“没有嗓子了,那就吃呗,再说吃辣椒又刺激又过瘾。”他这一说,徐青青还真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些“杂质”,好像年代剧中收音机调频不准伴随的“嗞嗞”声。
“那你还唱歌吗?你唱得那么好听。”徐青青放下筷子。
“不唱了。”童尧回得干脆。
“那多可惜啊,你的声音在咱们社团可是数一数二的。”
童尧摆摆手:“不说过去了,说说你吧。”
徐青青被这句话冷不丁堵住了,不知怎么接话。
童尧看着徐青青说:“其实你长得很漂亮,大眼睛,气质好,是越看越耐看那种,顺眼。”
徐青青“唰”地脸红了:“有你这么恭维人的吗?”
“不是我恭维,是真的好看。”
徐青青浅笑一下,拿了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童尧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继续从辣锅里捞羊肉。徐青青稍感意外,眼见烟头明灭之处,尼古丁燃烧后的青白色气体从童尧鼻孔喷出,迅速扩张,像一滴墨汁掉进水里,瞬间吞并占据了原来的空气,一下子就把他包围,困在其中。徐青青不由自主咳了两下。
旁边的服务员问要不要加汤,徐青青点点头。等水开的工夫,两人放下筷子,聊起播音社团的旧事,新闻组、文艺组,还有那位会调节气氛的学长,两人说着说着不由都笑了。徐青青想起散伙饭上童尧说起转专业的事,不知道他毕业后去哪儿了,此时想问,又怕不方便,毕竟童尧从见面到现在都没有提这方面的事。
水位再次下降,直到露出锅底潜藏的一两块香菇和西兰花,煮烂的豆腐也像鱼一样搁浅了。童尧问徐青青还要添点儿什么菜,徐青青摇摇头。童尧站起身,像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递到她面前。徐青青吓了一跳,忙问是什么。童尧笑着说:“别怕,这是咱们社团的记忆,留住那段时光的东西。”
“是吗?”徐青青有些犹疑。
两人出了门,童尧说要开车送她回去。徐青青忙说,自己骑电动车来的,路不远,还要把车骑回去。童尧也没再坚持,两人就此道别。
一排梧桐从人行道探出头,被橙黄的路灯在慢车道上分割得忽明忽暗。徐青青骑得很慢,双脚放在踏板上,看着缓缓倒退的树影,有种走在传送带上的错觉。她细细回放饭桌上童尧的话,若有所思。
回到家,跟父母打过招呼,徐青青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她把盒子放在写字台上,慢慢解开系绳,打开盒盖,一个精致的包包安静地躺在里面。一路上她都在想,和播音社团有关的会是什么东西,播音稿?活动记录?还是聚餐照片?总不会是童尧把机房的麦顺了一只过来吧。一只包包和社团有什么关系呢?想了半天,徐青青突然明白,自己是相信了童尧善意的谎言。她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傻白甜”。她打开手机搜了搜,确定是“古驰”的“酒神”款,价格快抵得上自己俩月的工资了。客厅里传来老妈喊她吃西瓜的声音,徐青青应了一声,边往外走边想:价钱贵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用这种方式骗自己收下礼物,算什么呢?
三
曹云妮光着身子从床上起来,披上冰丝吊睡袍,点上一支“苏烟沉香”,走到梳妆台前坐下,跷起二郎腿,吐出一长串“飞机尾烟”,开口问道:“你跟飞机上那女孩儿啥关系,你们俩很亲热啊。”
等不到回答,她继续问:“你是真睡假睡,问你呢!”
床上的男人翻了个身,不耐烦地回道:“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大学同学……普通同学!”
“切!哄谁呢?”曹云妮一脸不屑的表情,“那你下飞机躲着我干吗,还不是怕那个小妹妹看见你跟我在一起?”
“谁躲你了,人多走不到一块儿多正常啊。再说我听见你说在出站口集合,我不是去出站口找你了吗?”
“反正你就是不正常!”
童堯当年确实想转专业,倒不是因为对人文学科毫无兴趣,而是他知道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不好,岗位需求少,也挣不了大钱。转到他理想的金融专业并不容易,好几门重要的基础课要修,有绩点要求,还有名额限制。教材和辅导书童尧倒是买了,不过看书的时间比去电台的时间短得多。他清楚自己的音色有杀伤力,乐于享受女粉丝听他唱歌后的反应,沉迷于这种感觉带来的多巴胺,不,是内啡肽,对他而言,这已经超越了虚荣,简直就是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大四上学期,在徐青青刷完足够的题去报名公考时,被转金融专业失败打击了信心的童尧举棋不定,三心二意地备考本专业的研究生,等到考研失利再回头找工作时,却发现错过了重要的秋招。童尧没有一个像徐爸这样的父亲给他指导,他的父亲在他上中学时遭遇意外去世了,母亲经营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烟酒副食店,只负责每月准时给他打钱。
大四下学期,留给童尧的只剩下岗位远不如秋招的春招——他确实要抓住春天的尾巴了。童尧关注了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就业公众号,收藏了众多招聘平台,把其中的对口招聘岗位一一下载,日夜投递简历,期待邮箱被一封封回信破门而入。童尧在简历的特长一栏里填上“唱歌”时并不自信,他知道这和自己的专业看起来没有任何关联,但徐青青随口说的那句话给了他鼓励,“你很有才华啊”,唱歌算才华吗?但愿是吧。
好不容易有四五个笔试通知,童尧哪个都不敢轻视,哪个都想抓住,就像橘猫看见了好几个滚过来的小圆球。恰巧这些笔试都集中在一周多点儿的时间,童尧记得,那八九天他疲于应对一场又一场动辄两个半小时的考试,强度堪比清代考进士。一周后好消息传来,他终于进了“会试”——去邻省省会参加面试,邮件来自一家国企性质的城建设计研究院。本来童尧可以从容坐火车过去,没想到又来了一个笔试通知,时间改在了面试前一天的上午,童尧只好把火车票退掉换成机票,提前赶了过去。
童尧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等待。候机厅里,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甚至听见胃肠排空的声音,后来这种变化延伸到情绪,发展成焦虑。这时,一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他旁边,跟他搭话,说她刚刚查了,这种中小航空公司尤其是历史准点率低的,经常延误。童尧扭脸看了看女人,单眼皮,高颧骨,抹着一个约等于号似的红嘴唇,便礼貌地回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那女人拉开提包拉链,拿出两个小塑料袋包装的手撕面包,随手递给童尧一个。童尧忙说不用不用。女人说:“这算什么呀,活人总不能被饿死,别客气。”与其说童尧用手接过面包,不如说是他空荡荡的肠胃命令他接过来。天黑透了好一会儿,终于传来请乘客登机的广播。晚点整整五个小时后,飞机攒足了劲,一跃而起。
登机后,童尧刚坐下,一抬头,发现那女人正站在他身边冲他微笑:“真巧啊。”童尧瞬间明白了,也冲她笑一下,侧身请她过去。连日来的考试加上漫长的候机把童尧弄得精力透支,体力不济,舷窗外的漆黑恰好给他拉上窗帘,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但脑子里惦记着第二天早晨的面试,无形的压力让他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中,他似乎听见女人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说话,他根本没力气回答,偶尔听清了一句,又像是女人在自言自语,不用他回答。
飞机落地滑行后,童尧把手机切换回正常模式。一条短信“叮咚”一声抢先跳了出来,像开闸放水后跃出的第一条大鱼。短信是童尧预订的酒店发来的,大意是根据协议,房间为您保留到晚上八点,但您未按时入住,预订已经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