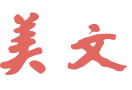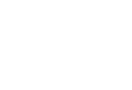一
翠湖,被看做是昆明这座高原城市的眼睛。如此比喻的是汪曾祺,他曾就读西南联大。联大的校址离翠湖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穿过几条老街旧巷就到,因而昆明五华山西侧的翠湖,当年便是联大师生课余时常去的地方。八十多年前的昆明,翠湖边宁静的茶肆,反射着亚光的青石板路,黄昏时分泛着柔和金光的水面,曾让多少联大师生流连忘返。离开昆明多年以后,汪曾祺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光,写下了《翠湖心影》一文。他在文章中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并说这眼睛善意、明澈、充满温情。
在我看来,翠湖也许更像昆明柔软的心脏。不仅是形状像人的心脏,更重要的是,散布在翠湖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几乎可以代表昆明这座城市文武兼修的品格。清代道光年间,云南都督阮元模仿苏东坡在杭州西湖修建“苏堤”,也在翠湖的南北向修了一条可以步行的堤坝:阮堤。这条堤坝将翠湖一分为二,就像是人的左心房和右心房。到了民国初年,主政云南的唐继尧也不甘落后,在翠湖的东西向修了“唐堤”。围绕翠湖,他们都想写点“文章”,留下名垂千古的东西。外地人来到昆明,时间允许的话,大体是要去看看翠湖的。就像人们到了杭州看西湖,到了武汉看东湖一样。城市中的湖泊,水的停顿,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异样的安抚。翠湖虽小,但到了昆明不去看看,就等同于没有来过昆明,或者说是白来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到处是彼此克隆的高楼,相互模仿的大街以及毫无个性的公园,像翠湖这样作为一座城市重要标志的地点越来越少。来到翠湖,环着湖边的步道绕上一圈,再从阮堤或唐堤上走一走,看一看翠湖周边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立即会发现昆明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仅博物馆性质的建筑,围绕着翠湖就有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起义纪念馆、聂耳故居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堂、西南联大旧址、朱德旧居等十数个之多,所以有“一池翠湖水,半部昆明史”的说法。说到底,翠湖就是昆明的灵魂所在,只要它在着,心脏一样跳动着,昆明便生动而明丽。
翠湖的形成,与滇池有关。有好奇的地质学家考证,滇池已有340万年的历史,水面最阔大的时候,几近一千平方公里,那应该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浩荡。后来便一路萎缩,渐渐露出东南岸的大片丘陵和平地。滇池让出的空间,孕育了云南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古滇国”。到了清初,滇池的水面还有数百平方公里,当时的云南文士孙髯面对滇池浩淼的水面,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而翠湖,是滇池逐渐向西南方退缩后,遗留下来的一块水面,它像是一支军队撤退后最終没能够跟上大部队的殿后人马,也像一段乐曲演奏结束后的余音。后来修建的昆明城,设计者以五华山为高点,将翠湖囊括在内。渐渐地,位于昆明老城西北部的翠湖周边,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汇聚之地。
在昆明,重要的文化单位和学校似乎都集中在城市的西北部: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昆明医科大学、冶金专科学校……其校址都在昆明老城的西北,它们离翠湖都不远。最近的是云南大学,可谓近在咫尺,正门就在翠湖的北面,只隔着一条马路。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其址是过去的云南贡院,那是明、清两代云南乡试的考场。三年一次的乡试,决定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云南各地怀抱梦想的考生千里迢迢赶来,住在翠湖周边的客栈,等待着人生春暖花开。贡院下面的一条街,因住了大量学子,便取名为青云街,意为祝福他们的人生能够由此青云直上。从明清到民国,一些达官显贵和文化名人,也看中了翠湖这块风水宝地,依山傍水,他们将宅第建在了翠湖周边,其中就有曾主政云南的卢汉,有民国元老、云南大学筹建时的名誉校长王九龄以及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
许多人第一次来到昆明,会觉得这座城市既柔软又温情。数十年前,昆明的城区面积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大量的老式建筑,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宁静、安祥的城市还没有形成热岛效应,夏天最高气温只有28度,人的皮肤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存在。有一个地理学概念叫“昆明静止锋”,它是云贵高原冬天的一个奇特现象。静止锋的西面,阳光灿烂,而静止锋的东面,则阴雨绵绵。昆明恰好就在静止锋的西面,与贵阳在地理位置上背道而驰,气候也大相径庭。所以这儿的冬天有长达半年的旱季,天空蔚蓝,中午的气温18度左右,早晚气温要低一些,但也只是让人稍微感觉到有些冷凉。昆明人在这样的气候襁褓里生活的时间久了,都不愿意离开,甘愿成为“家乡宝”。二十多年前的夏天,昆明夏天气温因城市的扩张和汽车尾气的无节制排放,温度突破了三十度,满城人大惊失色,报纸作为重要消息刊登。所以外地人到了昆明,就像是进入了春天的怀抱,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林木葱郁,好像是谁在这儿按下了春天的暂停健。尤其是到了翠湖周边,沿湖有高大的树木,湖中的阮堤、唐堤常年是花的走廊。更为重要的是,翠湖附近还有不少保留着昆明城市记忆的老街区,光听街巷的名字,你就知道它们“包过浆”。府甬道、钱局街、文林街、青云街、先生坡、文化巷、染布巷……从这些街巷名中,能够体会到昆明缓慢、柔软的一面。
我最初到昆明的时候,中国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还没有开始,昆明还在按以往的节奏按部就班生活。那时的滇池,湖水尚清,大地上的洁净镜面,反射着蔚蓝色的苍穹。盘龙江穿城而过,昆明人的母亲河,流水不腐,浇灌着两岸的庄稼。白天人们在河中淘米洗菜,夜里枕着这条清澈的大河进入梦乡。那时的昆明是大地上的床榻,从来没听说谁患上了失眠症或者抑郁症,唯一的缺点,也许是它缺少季节更替的明显特征,缺少冬天的萧瑟与夏天的狂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云贵高原,山中的平地被称为坝子,而昆明就落户在云南面积第二大的坝子里。高山之坝,群山共同抬起的山中平地,土地肥沃,是离天空最近的粮仓。这个坝子河道纵横,像浓缩版的江南水乡。除了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外,还有二十多条河流带着从天空接纳的雨水,注入滇池,形成大自然吐故纳新的生态系统。佴家湾、潘家湾、董家湾、螺蛳湾,从这座城市留下的一些地名中,隐约还能看到滇池曾经留下过的水痕迹。四百年前,徐霞客到昆明时,螺蛳湾还只是滇池边一处沙鸥翔集、螺蛳遍地的小渔村。可今天,它已是中国昼夜运转,辐射东南亚最重要的商贸城。我曾经在路过环城南路时,看到一幢高耸的建筑上,写着如此霸道的广告语:“昆明的螺蛳湾,世界的商贸城!”
可以说,千百年来,至柔之水浸孕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也塑造着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