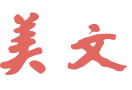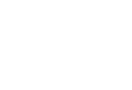君迁子
原来窗外的小柿子树学名叫“君迁子”,真是好听极了,令我肃然起敬,虽然它伴着我的日夜晨昏,婆娑树影给予我无限愉悦,但客观地说,我仍不知道它的何种气质或形态让它拥有了这样诗意的命名。
果实累累的君迁子,大部分枝杈举到了三楼邻居的窗台前,而离我的窗台则有两米之远,这让我对邻居无限羡慕,我只能从楼下经过时,偶尔折一枝上来而已,人家却可以随手摘星辰。
窗外这个生动活泼的绿树仪仗队正在抵抗着秋天,在变黄,变枯萎,即将一片一片地落叶,到了深秋恐怕就与我一一永别了。我无法想象一个视线里没有绿色的小楼之冬。这使我已经开始了离别的焦虑。就像一个深入的恋爱面临结束那样——可能还要更加残酷,因为明年春天的新叶,很清楚地不可能是这一批叶子了,这个告别是死亡之别。
小时候,每个黄昏都要拎两桶水到露台上浇每一盆花,年幼的小手臂努力地将清水拎上一阶一阶楼梯,到了露台上,总是先把水桶放下,喘一口气,赶紧对花们说:“你们一定渴了吧,别急别急,马上就来给你们浇水了!”我想象风中摇曳的花儿对我的出现欢喜雀跃,而当一瓢一瓢清水湿润枝叶和泥土,我似乎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一种盛夏饮水的清冽快意。我喜欢在浇水后流连花间,心里与它们有说不完的对话,而临下楼时,总要和它们挥手告别,想象它们如我一样恋恋不舍。我见花儿多喜悦,料花儿见我应如是。
这个童年的孩儿,至今仍栖居在我的灵魂里,没有一点变化。当年,生活在南方的她从未见过冬天会落光叶子的花草树木,对她来说,别离只发生在落花时分。而现在,却要感受与生活中的每片叶子之间,这样地一年一度的死亡之别。
下午坐在这里,看着树叶渐黄的窗外,有一种真切的悲哀。这些树的与我同在,构成一种真实的亲密无间,相比那些与我隔着时空、有时令我想念有时令我厌倦的人,究竟谁给予我更多快乐?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树们从未让我痛苦、让我厌倦、让我困扰、让我哭泣过。仅仅就这一点,它们是一个神话、一个充满精神抱持的存在。
夜晚的阅读
凉夜里裹着柔软的毛毯,坐在丝绒沙发上,读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读昌耀的诗集,读韩炳哲。
昌耀的语言,是语言之外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有边界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们无法描述这个世界,即使想描述,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而昌耀却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造诣,能够造出“合适的词”,用语言的超越去超越这个世界的局限。
我愿意每一天都这样度过,如马克思描述的一种理想生活:一个完整的人,应该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每个人都并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自由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个体从而能够为自己的兴趣工作,今天做这,明天做那,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上从事批判。这样的个体不会永远只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劳动导致的异化,和异化带给个体的痛苦。
而在马尔库塞的构想中,不仅存在着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还存在着一种能够提供高度力比多满足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令人愉快。他认为艺术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所以,艺术的力量、艺术的作用,就在于艺术对爱欲的解放。
所以马尔库塞宣扬:为爱欲而战,就是为生命而战。
诗 意
秋天几乎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