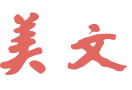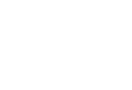一
赴崂山那夜的路上,大巴车颠簸得久久不能入睡。歪头一直看着田野上的茫茫夜色,大地仿佛消失了,偶尔出现在极远处的路灯、村灯萤火虫般跳荡、游走,一团团黑乎乎的树影似并无恶意的鬼魅急呼呼地朝身后掠去。我感觉游荡的思绪都被夜染黑了,一缕缕融化在深广的虚空里。
此时,初夏的手掌遍抚胶东大地,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在物候深处布散。崂山也已全然张开它拖曳的绿色裙裾,游人蜂拥而至,迤逦于它巨大胸襟的每个可以驻足的褶皱、纹理。一个伟大的道场变作了一座波浪起伏、心旌摇荡的花园。人们希望在他们出现的地方,那些古代的神仙也能同时出现,伸出一根手指为他们指点各类迷津。但只有山峰的手指从大地直插苍穹,寂然无语,应答一切。对崂山而言,没什么不是过客。一群群人走了,崂山还在那里;一片片云飞了,崂山还在那里;一树树花谢了,崂山还在那里。崂山永远峻拔。此在,空寂、不生、不死,只有绽放的当下。神仙们的昨天,在崂山永远都是今天,那些道场刚刚散去,便又与所有空间的道场再度共谋着另一次开始与继续。香烟缭绕之间,崂山不改亘古容颜。
二
古时,崂山却没这般热闹。顾炎武在《崂山志校注·序》(明·黄宗昌著)中说它“其山高大深阻,磅礴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即便如此,自汉至金元乃至明清,亦多有隐居、修道其中者,崂山道教的“家族谱系”更可上溯到齐地的方仙道、黄老道、黄老之学。所以,“三围大海,背负平川,巨石巍峨,群峰峭拔”(《道藏》)的崂山自古即汇聚了齐地浩浩汤汤的“仙气”。《太平寰宇记》有“秦始皇登劳盛山(即崂山)望蓬莱”的记载。始皇东巡,无非为了访仙问药(也有捎带寻根问祖一说),举全国之力而为一己之不死。因为一个皇帝的私欲,崂山才第一次被大规模地打扰。对此,顾炎武愤然有言曰:“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一郡供张,数县储偫,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始皇劳民伤财,崂山由是得“劳山”之名,正所谓“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但他也许无意中给崂山“开了光”,证明此处确有“仙迹”存焉,因处东海之滨,因距人间邈远,因清寂到除了看看东海,便是餐餐紫霞,神仙而外,凡人怕是居大不易吧。就连批评秦始皇的顾炎武不也赞叹崂山是“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吗?始皇心向往之,良有以也。秦之后,汉之张廉夫、五代之李哲玄、北宋之刘若拙、宋元之全真诸子,皆择崂山修真悟道,所以,“神仙窟穴”的古称的确名副其实。这些“不凡”的人中,最著名的大概要算丘处机、张三丰与憨山德清了。邱长春云游崂山时,干脆给它定名“鳌山”,“以為栖真处”。张三丰更是从海岛带来耐冬花植于庭前,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绛雪”,“正月即花,蕃艳可爱”;崂山还有张仙塔、邋遢石等遗迹、景观附会其羽化故事。憨山到崂山后于树下掩片席为居,却不以为苦,七个月过去,始有人帮他结庐、造庵,他却言:“吾三椽下容身有余矣!”果是大德气派,身外无物,则不劳铺张。我觉得这几位高人中,张三丰更像个诗人,把养花种草当做一种修持的美学,也为崂山植物增加了品种。试想:寒风猎猎,大雪空山,谷中庭院中,唯有绿叶红花更其静定、绚烂,如肉与灵的孤绝火焰,照亮着寂灭且永恒的道途。那番情境,有几人体验得到?
道人、佛僧们在遥远的时空中出现,即使在“地高气寒,又多烈风,非神完骨强者,不敢久居”(明·蓝田《巨峰白云洞记》)的冬季,他们仍能衣衫褴褛、枯瘦如柴、目光炯炯、道骨仙风地步上山巅。他们不是一步步登上去的,而是慢悠悠飘上去的,然后,从容自在地坐在石头上、树木上、云朵上,一坐就是天荒地老、地老天荒,一坐就变成了石头、树木和云朵,终于化成一道光,倏然而逝,无声无息。在那些几乎死去的古书里,我读到过很多仿佛脱离了肉体累赘的深奥言说,玄幻而渺远,我相信其中保留了某类存在的真相。修道者并行于两个世界,文字记录描述的不过是他们在人间的投影罢了。然而,作为俗人,我们却仅有一个世界,从没离开过山下的烟火气。不过,即便作为俗人,偶尔也需要瞥一眼山上的紫霞,体会一下将尘世遗忘的滋味——尽管不可能盯着那高处的紫霞看上一辈子。秦始皇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他可以为崂山写下一首诗:“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不过是借李少君忽悠汉武帝的话吹吹牛而已,学道不成,只好写写诗、用用典罢了。巡游求仙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只皇帝做得;吹牛夸张的恣意出乎伟大的想象力,仅诗人可为。而今天的我们,可能仅剩下跋山涉水的耐力和盲目了。
三
曾三访崂山,相隔二十余年。第一次,从沙子口抑或王哥庄的某处山脚下往上攀爬一小时,几近躬身踯躅,不断左顾右盼,如前路时被阻断的蚂蚁,脚力十足地在山体襞褶里辗转移动。抬眼间,满眼绿色,浓稠如刚刚涂抹在画布上的油彩,感觉迷失在一片巨大的叶子上,寻不到折返之路——那些棕红色岩石的“披麻皴”如苍老的树皮般在远处裸露、嶙峋。那次我们是去寻找“海底玉”,顺便在山脚下走了走。我对崂山的兴趣远大于“海底玉”。“海底玉”即崂山绿石,产于崂山东麓的仰口湾畔,按说属于稀缺资源,但我当年的印象却是——这东西多得到处都是,根本不稀罕,在村子里转悠,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堆成一座座小山的“海底玉”原石。数百年的玩赏历史,好似突然又“热”了起来,一时成为市场新宠,叫响大江南北,也不过是炒作的生意。客商们像发现了新大陆般接踵而至,导致过度开发,崂山突然更换了“面目”,变作了被市场经济拖出“深闺”的“暴发户”。当地有个村民告诉我,一小推车“海底玉”原石不过一百多块钱,简直是暴殄天物。明黄宗昌《崂山志·卷六》中有言:“绿石,出丰山,邑多好之,而侄孙贞麟之绿屏为难再得。”这些蕴藏于海滨潮间带的石头,因为开掘技术的进步,遭殃甚重,我亲眼所见的比黄宗昌所述之绿屏更庞大的物件也不在少数,还有雕成弥勒佛的,大大小小、胖墩墩地坐满农户的半间屋子,个个都是“容天下之事,笑可笑之人”的完美表情。我真怕崂山下面都是“海底玉”,若按当年的开发架势,不消几年,就可能是一片狼藉。
第二次是从景区正门进入,缓步至玉清宫。其实,最迷人的景致出现在沿海公路两侧,移动、旋转的山麓,林荫与碧海、云霞与礁岩,像空间镜像上闪回的最美画幅。之后的漫长行走中,崂山始终以冷峻而泰然的方式打开,路旁清寂的树木,在繁盛中隐含着一种落寞而沉思的表情,像是躲在时间深处的等待与持念。洁净的山道深掩于植物的气息里,每一步上升都沐浴着阴凉,却听不到一丝季节的回响,好似时间静止了。仰头观望,树木、花朵、石阶、院墙、道观、神像,皆沉默无语,空气在它们上边睡眠、扩散、垂落,阳光于若隐若现的缝隙间栖止、晃动、漂移,就像道士们的身影与表情,携着恍惚、缥缈又轻盈的节奏闪过。崂山是一个让人放下执念的地方,它的陈述只有一个词语:无为。因为无为,一切才如此茂盛,连潮湿的地面与方砖上的苔藓也茵茵如毯,从未被人踩踏过。蜂蝶和鸟儿在花丛里、树叶间、房檐下飞来舞去,像是在展示时空的无目的性或合目的性。下清宫茂盛的耐冬让我想起韬光尚志以为清虚元妙的张三丰,好似他刚刚洒扫完庭除,身影在枝叶间一闪,就不见了。古书有言:“夫古之至人,其动也天行,其静也渊默。” 大概就是说他这样的人吧。虽居崂山之下,与下清宫未必有什么瓜葛,但他移栽的植物却蔓延整座崂山,枝叶芳菲,如他穿越时空的玄想。其实,下清宫乃憨山所留禅趾处,明高弘图《劳山九游记》有记载:“诸劳皆道院,上人(指憨山)于此起禅林……”坐在半路的石阶上看小径蜿蜒,那一刻,我感觉有些恍惚,不见憨山,不见邋遢,不见古人来者,却在时空的景深处,看到了自己的虚影,被花树与殿宇的虚影笼罩着,一寸寸沉入万物之渊默,心相与物象,实无任何差别。当夕阳敛去大地的光泽,山下的城市华灯闪烁,不知怎的,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出离”之感。
第三次登崂山,全然是享受松松散散的宽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如禅悟,如随意的翻书,脚步跟着感觉走,了无牵挂得很。那是从背面山阴进入北九水,行不多久,便和几位好友在一池碧水边的小亭子里谈天说地,虽是初夏时节,景色蕃盛,所见也不过乱花迷眼,清香蔌蔌,杂树欹斜,翻风自乱,并无甚拈心留意处。却唯独对北山门旁的农家宴记忆深刻:金黄色的炒笨鸡蛋、嫩绿的崂山蕨菜、香喷喷的炖柴鸡、味道浓郁的蘑菇、爽口清脆的桔梗……都是山里的道地土货,味道足令人惦记多日,以至有朋友兼诗人名“华清”者建议:大家凑钱买栋山间别墅,退休后来此度假,偶尔寻访一下崂山道士,学学长生不老之术,岂不自在快活?……嘻嘻然谈笑间,捋一把胡须,仿佛将希望与妄想都留给了以后的岁月。
三年过去,我已非我,崂山依旧乎?
四
还是从沙子口登山,完成一次对崂山的纵向穿越。
晨曦初露,前方一片微亮暗蓝的天光。我们抵达了“大河东”。这也许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只见一条很窄的公路深入到一片稠密的玉米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