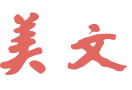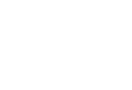武安街四号,是父亲的第一个家,他生于斯,长于斯。
武安街,位于江苏兴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兴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之所以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父亲是兴化人,于是,我也跟着是。在我小时候,要填各种表格,必有“籍贯”一栏,“江苏兴化”不知填了多少次,而当年并无“出生地”一说。当年,中国也没有颁发身份证,我们的唯一身份证明是户口簿,上面也同样只有“籍贯”而无“出生地”。依此,我是“兴化人”无疑。为什么说是符号而不是家乡呢?因为兴化对于出生在上海的我来说,只是一个地名,并无感性认识。父亲也不跟我们说任何关于兴化的事。
即便如此,那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总有一些来自兴化的人和物,让我感知它。
先说人。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和四位叔叔先后离乡。父亲李安祥,是老大。他们有七兄弟,二叔安石、三叔安乐在上海,四叔安舒在无锡,五叔安全在贵阳。父亲说起他的弟弟来,称呼很有意思,因二叔住在耀华路,叫他“浦东”,叫三叔“老三”,叫四叔“无锡”,叫五叔“贵阳”。用地名来叫人,实在有趣。六叔安荣和小叔安理在兴化。当年,五叔所在的贵阳,是远在天边了。无锡、兴化虽然不远,走动也很少。这样算起来,我在兴化的亲人,有祖父、祖母和六叔、小叔。祖母在我有记忆前,是来过上海的,但她不幸中风卧床,我后来没在上海见过她。祖父大约一两年来一次上海看看儿孙,他话不多,谈吐平和。弟弟长得浓眉大眼,深得祖父喜爱。祖父专门带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样的待遇,在祖父的儿孙中,是唯一的。这照片是我们大家庭拍得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一张。它一直放在家里的显眼位置,我看了,不无忌妒。我和祖父的合影,要晚很多年,直到我读大学。年过八十的祖父突然驾到,我们在复旦的毛泽东像前留影。小叔在我小时候,还是单身,来得最多。他长得斯文白净,与上海人概念中的苏北人不同,很是获得上海亲戚、邻居们的好感。他比父亲小二十多岁,看到大哥颇有敬畏之意,对我们完全没有长辈的架子,我和弟弟很喜欢他。六叔,先按下不表。
再说物。首先要说的,是棉鞋。那,可是祖母亲手做的。当年,最小的堂妹尚未出生,祖母有十个孙子三个孙女,她每年给每一个孙辈做一双棉鞋。我并没有在祖母身边生活过,没见过她做鞋的样子。但也能想象出,半身不遂的老人家一针一线纳鞋底,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十三双,真是不小的量。有的孩子,祖母从来没有见过,并没有听他们叫过一声“奶奶”,但每一个孙辈,都享受着祖母的温暖。当然,儿时的我们,是不懂得珍惜的。我穿着祖母做的棉鞋瞎玩,鞋头常裂开口子露出棉絮,补了再穿。步入中年后,我常年穿“内联升”布鞋。踩着手工纳的千层底,感觉温暖而踏实。其次,是六叔的车。六叔是七兄弟中唯一的军人。他是坦克兵。他开的坦克,是苏制,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开坦克,多么帅气啊!我们没有机会坐六叔开的坦克,但却坐过他开的卡车。六叔退伍后,当了司机。开大车,也开小车。当年,司机是很吃香的,在兴化小城更是。六叔开着卡车来上海,便是我和弟弟的节日。他带我们兜风。我们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俯看街上的行人和骑车人,别提多爽了。第三个要说的,是螃蟹。我们小时候,是物资匮乏时代,肉、蛋、鱼,都凭票。但河蟹还是可以随便买的。每到秋天,农民将蟹用稻草绳扎成一串串叫卖,但不知为何,个子都不大。一次,六叔开车来,带了一袋蟹,只只足有半斤,那是我儿时见过、吃过最大的蟹。
因为这些人和物,兴化这个“符号”便有了温度。我们也生出去兴化看一看的念头来,但不知为何,父亲总是不带我们去。二十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父亲突然命二叔领我和弟弟去兴化,我们相当兴奋。父亲先把我们送到浦东,交给二叔。在二叔家玩了几天,随他前往兴化。我们先是坐绿皮车到了无锡,住在四叔家。这是我唯一一次到四叔家。不料,二叔在无锡心脏病发作,取消了计划,带我们打道回府。我和弟弟失望极了。
大概父亲也觉得,总是应该带妻儿回一次故乡的。1973年春节,终于成行。促成这次兴化行还有一个原因,六叔来上海出差,我们可以搭他的车。一下子省下四个人的单程车资,在当年是相当令人心动的。那年,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回兴化,第一次回武安街,也是唯一一次住在武安街四号,父亲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