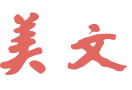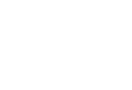八字门是岳州郊野的一个地名。这里根本就没有一张特别的门,但对于我来说,三十年里,始终有一道隐形的门,在控制和激励着我的人生。我大半辈子的经历,细想起来就是与时间和命运不断搏斗,然后通过一道道无形的关卡,慢慢接近和抵达自己的理想。
三十年前,我还只有十九岁,从两百里外的大山深处丢下教鞭,跑到岳州城里来寻找内心向往的东西——依靠文字养活自己的肉身也养就自己的精神。说得通俗点,就是想到城里找一份与文字相关的体面工作,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我,已教了一年的小学,在省市报发表了几十篇副刊作品。从厚厚一本的样报剪辑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辽阔的未来。我觉得逼仄的大山已容不下我日益膨胀的野心,而岳州城里的报社,才是我安放灵魂的最佳处所。我信心百倍地来了,哪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的朋友就是报社领导,看都不看我的作品,只反复强调复旦新闻系的应届生他都没有接收。从他鄙夷与不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单薄和寒酸。我只得退而求其次,央亲戚帮我找一家单位做文秘。费尽周折之后,城郊八字门的一家工厂接纳了我。从此,我的人生就与八字门有了不解之缘。三十年里,我换了多家单位,辗转几个城市,但最终还是落脚在八字门。我感觉八字门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隐喻,我的一生似乎都逃脱不了“八字”的控制。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到八字门报到时的场景。那时节,岳州城刚刚被中央列为沿江开放城市,城郊新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我那在市计委工作的亲戚,同时兼任开发区某部门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开发区今后会不得了,而我要去的那家工厂,则是这里首家冒烟的企业、首家年产值过亿的实体。总之,这里遍地黄金,通江达海,前程似锦,远比到报社做聘用记者写几条狗屁消息强。我将信将疑,先坐公交,再转短途,又换三轮,迎着深秋微寒的晚风,充满向往地来了。三轮车夫将我丢到暮色中的一处荒野,说八字门到了。我问工厂呢?他说鬼才知道。我抬头张望,只见推平的土地上长满一人高的茅草,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一阵秋风吹来,瞬间就将我淹埋。我突然难过极了,感到自己有如一粒尘芥,刚刚好不容易从深山中飘出,一不小心又被人扔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卑微的我们,连被人发现的可能性都极小,哪里还敢去奢望自己的理想?正在我急得想哭时,亲戚打电话喊厂方来接我的帆布吉普找到了我。我这才知道,我的目的地还在几里之外的蓬蒿深处;而我的理想,可能已距我万里之遥。
收留我的工厂是一家挂靠在政府的集体企业,实际控制者是一个私人老板。他以过人的眼光和灵通的信息,早在十几年前,就以极低的价格在八字门的荒山野岭上征得几百亩地。如今,他旗下已拥有多家实体,据说成了全市的首富,单是在八字门这片土地上,就建有一家年产万吨的饲料厂和一家专供出口的保健品厂。我来时,饲料厂正与一家国有大厂、一家金融机构,三方发起组建注册资金380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3800万元,现在看来是个小数目,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大得吓人,一个穷点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这么多。怪不得我亲戚认为这里堆满了金山银山,执意要把我安排进来。然而,在我的眼里,却只看到了一片枯黄与荒芜。
那时的开发区,白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晚上就变得黑灯瞎火,死寂冷清。在我们厂区周边几里的地方,除了没来得及推平的山包上残存几栋人去楼空的建筑,根本就看不到人间烟火。听老员工讲,离我们最近的单位,是好几里外的火葬场,在巴陵东路没有修通之前,进出都得经过这个让人胆颤心惊的地方。现在巴陵东路是拉通了,但进出厂区的道路,只是拖货汽车从茅草丛中碾压出来的一条临时土路,坑坑洼洼,高高低低,歪歪扭扭。平时要想进趟岳州城,如果没有便车,得先沿土路行走一里多到巴陵东路,站在路边等上半天,运气好时能挤上临近县区进城的长途班车,运气不好时,就只能吃一肚子灰尘又黯然打道回府。进城后如果下午五点前没有搭到车,那就只能步行十几里摸黑返回。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区的陌生之地,我年轻的心一下变得苍老。刚来的那段日子,下班后我常常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厂区周边的旷野里行走,走着走着就陷入到焦枯的茅草深处,分不清方向,也看不到出路,而天色又渐渐昏黑下来,我突然感到无比孤单和忧伤。我不想在这里荒废自己的青春,暗暗开始谋划如何逃离。
谁知我在这一干就是四年。之所以待了这么久,并不是我爱上了这个地方,而是我没有能力脱离它——我被工作和现实绑架,动弹不得。进厂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老板的随身秘书,提包、买单、挨骂、写材料,从早忙到晚,连撒尿都要跑步前进,哪里还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前程与理想?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似乎把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灵魂都卖给了他,除了炮制出大量天花乱坠的材料,就是跟着他天南海北地飞,声情并茂地吹,地动山摇地喝。他有一次骂我时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会写文章的人多得很,你离开了我,就狗屁都不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刚给他做秘书,他就给我开了四百五十元一月的工资,差不多是我教书时的三倍,甚至比我那副处级的亲戚都高。除了工资,还有大量的补贴和奖金。这年年底回家过年,只短短几个月我就给了父亲三千元钱,相当于他在信用站做会计两年的工资,他惊得不敢接。我知道,我和我患癌的父亲都需要这些钱来维持生存与生计,有时甚至还需要维护一下心底的体面和虚荣,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是在岳州城里,不可能还有谁会给我更高的待遇。在金钱与现实面前,我只能妥协,只能让精神和理想暂时退场。跟他做随身秘书的这一年半里,我没有写过一句属于自己的文字,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曾经把写作视为生命。只有从报刊上读到熟悉的文友的作品心里酸酸时,我才知道灵魂深处,还是需要某些与物质无关的东西来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