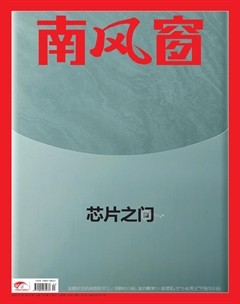2023年的大国政治里,“去风险”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从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这一概念,到今年5月七国集团(G7)日本峰会上写入文件,“去风险”开始走入转换为现实政策的阶段。
G7广岛峰会后发布的公报指出,成员国将“协调彼此的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方式,以多样化和深化伙伴关系为基础,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并强调,成员国的政策方针“并非旨在损害中国,也不寻求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经济韧性需要去风险和多样化,将减少对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
纵观公报全文,“中国”一词出现了20次,不仅可以看到美西方对华政策最新的集体性表述,也不难发现美欧政策协调中的矛盾性和两面性。一方面,G7国家领导人表示,“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经济规模,有必要就全球性挑战和共同关心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又污蔑中国存在经济胁迫、非法技术转让等行为。
鉴于G7是美西方最为重要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在其公报中载入“去风险”一词,并将其与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预示着美西方对华方略的相关表述和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美欧妥协的结果
在“去风险”成为新的政治流行语之前,西方世界用得最多的是“脱钩”。从字面意思看,“脱钩”指的是解除两个原本挂钩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从逻辑上讲,“脱钩”的前提是“挂钩”。在中美关系上,一般认为这个“挂钩”的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最终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突出象征。
这一进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发生裂变。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中国被美国界定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华“脱钩”实质上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政策选项。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同盟。特朗普并不看重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同盟体系,认为这导致美国负担过重,让美国吃亏了。而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显著标志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盟友关系,为此甚至不惜鼓动乌克兰危机。
不过,在对华关系上,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日渐发觉的问题是,收益和成本越来越不对称。不少欧洲领导者认为,欧洲没有必要为了帮助美国实现其称霸目标,而损害自身的利益,这一点在法国、德国等欧洲的核心国家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欧美之间的利益差异和战略目标分歧是长期存在的。20年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一书中有如下概括:“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卡根断言,冷战结束后,美欧之间的分歧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关于权力的性质和目标方面。“由于美国过于强大,而欧洲显得弱小,美国人更相信实力原则。对欧洲来说,软实力和制定规则才是欧洲应该努力的方向。”
卡根甚至预测,冷战时期形成的大西洋两岸一体的西方阵营已不复存在。回头看,卡根的这一预测有所夸大,但是就美欧之间的差异而言,卡根的论断仍立得住。
冷战结束以来的30多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下降态势,但西方内部却呈现出一种新的权力转移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总量占发达国家的比重,从1992年的30.8%上升至2022年的44.2%,净增13.4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占比从18.9%下跌至7.4%,欧盟从34.5%下跌至28.9%。
不少欧洲领导者认为,欧洲没有必要为了帮助美国实现其称霸目标,而损害自身的利益,这一点在法国、德国等欧洲的核心国家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因此,一定程度而言,美西方内部的权力进一步向美国集中,欧洲和日本衰落,这进一步凸显美国通过凝聚西方权势护持霸权的迫切性。从全球来看,欧盟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92年的28.8%下跌至2022年16.6%。显然,对西方其他成员而言,霸权的收益却不一定会合理地分配给他们,追随美国霸权始终不是最优的选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欧洲选择了另一种处理对华关系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底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对华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