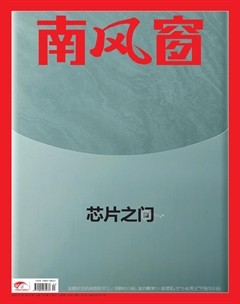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晶体管诞生在美国最大的实验室,它的制造者或许料到了这个小小的器件注定前途无量,却不能预测此后芯片的发展会经历怎样曲折而惊险的旅程。
印度有一个传说,有关指数级增长是如何把一个不起眼的起点导向庞大而不可测的结果。向国王领赏的数学家要求在棋盘的格子里每次多放一倍数量的大米,从1粒米开始,最终所需大米的数量穷尽国王的想象也不能满足。
这几乎是芯片发展的模型。
快速增长的代价是,芯片技术对迭代的要求也给自身设下藩篱,就像一种自我诅咒,让它不断面临着想象力的局限、物理学的边界、难度与速度之间的悖论。
芯片的竞争,本质上是经济与科技实力的较量。在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历程中,确有举国之力倾注其中的例子。但在某些特定时刻,技术飞跃又依靠一个个天才的构思。
为了推倒芯片发展征途上的各种路障,一个个破局者出现,在他们的故事中,芯片的历史,由纯粹而热血的智识挑战构成。走过历史的困境,我们才能知道,如何解绑我们对芯片未来的想象。
硅谷前史:冷战与嬉皮士
1947年,沃尔特·布拉顿和约翰·巴丁在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点接触型晶体管。在此基础上,1951年,威廉·肖克利发明了结型晶体管。三位科学家因此共享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彼时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一个小小的元件将会成为电子信息时代的先声。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192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将西方电气公司工程部与AT&T研发部合并为一个独立的科研中心,以电话发明人贝尔的名字命名。对当时很多科学家来说,这是一片圣地,他们可以在里面做任何异想天开的研究。
没有任何一种自由是无根的。贝尔实验室背靠的AT&T当时在美国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高昂的利润让他们能够为贝尔实验室提供每年至少10%的基础研究经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贝尔实验室提供大量资助,军事部门成为贝尔实验室的最大客户。最开始出现晶体管的发明需求,是因为二战时期基于真空管的设备和军舰有一半以上在操作当中存在问题。1947年之后的5年内,全美总共生产了9万个半导体晶体管,几乎全部被美国军方收购。
来自企业和军方的资金支持,保证了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有趣的是,这部最开始由战争史支撑起来的科技史,正在朝向叛逆史转变。如果说贝尔实验室最早培育了一批不用操心钱的科学家,那么接下来,自主创业的风潮很快会将“财富”二字带到这些科学家面前。
1955年,不满足于自己的名字只能与基础研究挂钩,他还希望自己作为富豪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在旧金山郊区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半导体公司。
据说肖克利在报纸上用代码的形式刊登招聘广告,为自己招到了当时业务水平最顶尖的工程师。强强联手的局面本应很快能为肖克利带来他想要的名利,但是他为人刚愎自用,有做基础研究的头脑,却没有管理企业的才干。因为公司管理涣散,业务下降,1957年,肖克利手下8名工程师因无法忍受他的控制,离开公司自立门户,创办了一家名为“仙童”的半导体公司,这家公司被认为是硅谷(Silicon Valley)的雏形。“硅谷”正是因作为半导体原料的高纯度硅而得名。
IBM的工业设计顾问向库布里克提议:你电影里的计算机太小了,这不符合常理。库布里克说,不,越来越小是计算设备未来发展的真正趋势。
仙童创立之前,半导体电路中的各个元器件彼此独立,单个晶体管、电容和电阻插在电路板上,还需要另外的线路连接。在技术爆发时期,半导体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迅猛增加,再对单个晶体管进行手工连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仙童开始致力于集成电路的研发,他们设想能够直接在一整个硅晶表面同时做出晶体管和它们之间的导线,从而实现大规模生产—芯片,就是这样一块含有集成电路的硅片。
1957年10月4日,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升入太空,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军工和科技压力,就在这时,仙童收到了第一笔大订单,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62年,仙童的芯片被用于阿波罗计划。
然而,硅谷的工程师们隐隐感觉到,芯片的未来不止在火箭上。
1963年,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面世,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工业设计顾问向库布里克提议:你电影里的计算机太小了,这不符合常理,“发现号”飞船的计算机至少应该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库布里克说,不,越来越小是计算设备未来发展的真正趋势。
诞生之初有5层楼高的超级计算机,正在一代一代地接近库布里克的设想。
自肖克利之后,从原东家出走自主创业几乎成了硅谷的一种传统。由于与投资方之间矛盾不断,仙童公司出现离职潮,开始向整个硅谷开枝散叶。
制作出第一块硅基芯片的罗伯特·诺伊斯与戈登·摩尔于1968年合作创办了英特尔(Intel)公司。被仙童解雇的杰里·桑德斯于次年成立了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这两家公司打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芯片领域成了“死对头”。
乔布斯说,那时候的仙童就像一支成熟的蒲公英,硅谷到处都是“小仙童”们新开的创业公司。
与硅谷一同蓬勃起来的,还有嬉皮士、摇滚乐、摩托车。充满叛逆精神的60年代,工程师们比他们任何一代前辈都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與私人财产的获得,一位员工在仙童的离职调查表里写下:“我……要……发……财……”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硅谷不仅是新科技的摇篮,也成为了工程师们追寻财富的应许之地,肖克利没能达成的愿望,将被后来的硅谷人实现。
未来,人们希望拥有更轻便的收音机,希望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台电脑,希望在尽可能便携的设备上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时代精神的转向为电子产业创造了前景,反过来,电子产业的发展也即将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越来越小的器件给每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私人空间,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会被电子产业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