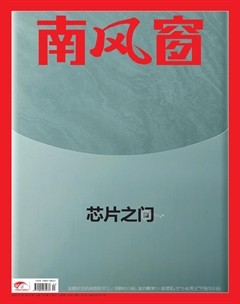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变化,似乎成为了唯一确定的不变。
疫情、通货膨胀、地缘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最终引向了更大范围的地缘经济和金融分裂。金融制裁和经济摩擦不断升级,货币武器化的趋势明显,显现出来的风险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去美元化,走向多货币的世界。
脱钩、去风险化……类似的概念陆续被摆上台面争论,似乎所有人都正致力于为全球分裂做准备—多数时候,只是建起高墙后是否要为了交流留一个门的区别。
流动性减弱后,世界版图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放缓的全球经济,正倒逼原本适用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改变。但我们仍不知,“反自由主义经济常理”的趋势,长期会给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2023年7月,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至3%;但在2023年10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在维持2023年经济预期的基础上,又下调了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期至2.9%。报告中,IMF写道:“(这样的增速)远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
而世界银行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则更加保守一些。2023年1月,其将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1.7%,7月则上调至2.1%。
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是否有重建秩序的可能?身处其中的中国要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建立经济韧性?2023年10月29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周年全球年会期间,南风窗与IFF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就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可能性,进行了对话。
全球化,再全球化
南风窗:你曾以美国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为例,提到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指标。结合各大机构对2023年全球经济的预期,你如何判断如今的全球经济形势?
陈兴动:与以往确定性较强的全球经济预期不同,今年市场因全球分裂,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相对不一致。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慢慢从合作走向对抗,并最终影响到贸易。
从全球变化过程来看,全球化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领导着该体系的西方国家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后期,其经济反而脱实向虚,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反全球化由此开始。
但同期,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利好。全球化与行之有效的政治优势、劳动力素质优势和土地价格优势等相结合,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当中国实现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展进度时,就希望改进现有规则。
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并开始调整政策—从介入中国,变为介入、接触与遏制相结合。到2018年时,美国确认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政策由此转向更加系统性地遏制中国。
世界分裂由此促成,全球经济也开始碎片化。人流、资金流都被人为地割断,世界经济从一个比较充分竞争的状态,转向了保护主义条件下的贸易状态。适用于过去40年经济形势判断的指标,可能就需要重新审视。并且宏观经济学近年来式微,还未形成新的判断底层,世界也处于急剧变化的过程中,还未稳定下来。这个阶段仍较“乱”,大家都在观望。
我个人的判断是,尽管美国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形势良好,但不太可能迅速扩张;发展中国家应当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由此,市场对于经济形势的焦虑,会比1至3个月前少。
可以看到,第三季度增长数据是积极的,但支出方面仍然承压,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估计都达不到。第三季度生产法的积极增长或有4.9%,但支出法恐怕低于3%,压力比较大。
既然全球化不可能被完全打破,小规模全球化也难以运转,那么,探讨再全球化就很有必要。而新的全球化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由西方国家完全领导。
南风窗:在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议题上,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可能性被着重讨论,你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新的全球化?
陈兴动:首先回顾下全球化历史。早期全球兴起了反全球化风潮,认为世界已经过度全球化,需要改变;由此进入全球发展的第二步,去全球化;近期已经进入了第三步,脱钩。这会导致“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状态。
但寻求脱钩的国家发现,其仍然需要愿意投入产业的工人,也需要中低端产业的支持,无法与其他国家完全割裂。同时,中国等原先在产业低端的国家也在向高端进发,性价比高,竞争力强。此时,去风险化概念出现。
但什么是风险?风险在什么地方?准备如何应对风险?
比如,美國提出了“小院高墙”,确定在芯片、AI、量子和计算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