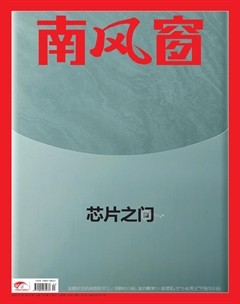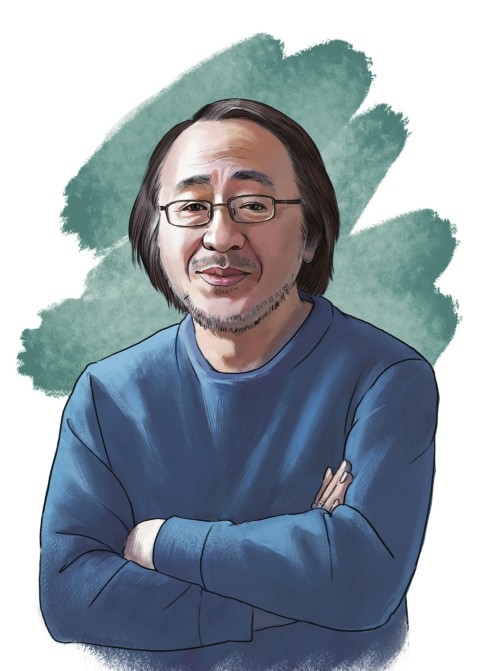
2023年10月21日,时隔两年多,我再次在位于台北市的“老咖啡”见到唐诺。而隔天他就要前往北京,这是时隔5年后他第二次担任“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
没什么变化,唐诺还是打扮得很随性,站在吸烟区吞吐一根香烟。我则点了一杯“招牌拿铁58号”,那是第一次来这间咖啡厅时唐诺推荐的。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 年出生于台湾宜兰。他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人创办著名文学杂志《三三集刊》,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等作品。
我第一次见到唐诺,是因为简体版《声誉:我有关声誉、财富与权势的简单思索》在2021年出版,这次则是于今年10月出版的简体版《求剑:年纪·阅读·书写》。
“刻舟求剑。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们想用它来找掉落时间大河里的某物。”唐诺在书中写道。他更是说“时间是我真正期待的”。然而,刻舟求剑,终究是寻不着剑的,所以这“某物”又究竟是何物?
当年纪成为阅读和书写的变相
南风窗:一直以来,你写作的主题都围绕着“阅读”和“书写”,这本新书中加入了“年纪”,可以请你谈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吗?
唐诺:写这本书,是发自一个意念—我想知道在我这个年龄,老年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即阅读和书写,但我的年纪却一直在改变。所以,我把“年纪”作为一个“X factor”,加入我的阅读和书写,这样我会产生什么变化?与此同时,我写出来的东西跟以前会有什么差别?
也许不容易看出来,因为这毕竟是微妙的,但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例如,我过去谈张爱玲跟现在谈有什么不同?其中可能有个人的,也有从思索跟阅读累积产生的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时间本身带来的。而张爱玲写《小团圆》《雷峰塔》《易经》这三本书时也有了年纪,不是她年轻时写的东西。看的时候我就会想:她在想什么?她可能想说什么?这个是我三四十岁的时候不容易体会的。随着年纪的不同,注意的东西会产生变化。
南风窗:书名是“求剑”,你希望从时间的大河中打捞出什么?
唐诺:这个题目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本来的题目是四个字—刻舟求剑,真正打动我的是这个老成语。后来出版社觉得提炼出“求剑”两个字比较好,其实让我选的话,我会选“刻舟”,因为这才是我做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刻舟求剑”讲的是一个愚人,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事,不一直都是这样?写作也一直是这样,你写到童年、写到生命的某一段时光,船已经老早开走了。
在我看来,所有的书写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写的时候,船都已经往前开过了,开多远了,那个东西就掉落在那里,你还能捡得回来吗?当张爱玲回过头去写她最后的那三本书(《小团圆》《雷峰塔》《易经》),那是她年轻时的记忆,那个船都已经开了几十年了。
所以书写的时间差和延迟不都是这样?也不止是书写,我们生命里头很多事都是这样。你说它是愚行,它也真的是愚行。所以我觉得“刻舟”比较适合我。
而打捞的,对我来讲,是在时间某处的东西。说回忆,也不是,好像是个人的生命境遇,有些东西我们还可以辨识出来,而当我们有幸再找到它,它本身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原原本本的吗?
时间会产生一种荒谬感,举个例子,朱天心就很受这个问题的压迫和煎熬。
比如,你对现实有较大的关怀之心的时候,你会思考自己写东西到底是为什么?朱天心为一只猫请命,但书写有时间差,当你把这个讯息顺利传递出来后,那只猫可能已经没办法救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