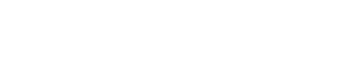中国广州市与美国剑桥市之间的时差是12个小时,如若不是要采访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我想我大概率不会特地去查询这一信息。晚上9时,广州的天空已是一片深色,原本只有我在的视频会议,出现了浦洛基的画面。与既紧张又疲惫的我不同,浦洛基显得闲适自在很多。
对沙希利·浦洛基这一名字感到陌生的读者,也许会好奇他的身份。可以加在浦洛基名前的头衔有很多,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席教授,也是哈佛乌克兰研究院院长,但更为大众熟知的,是他作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作者的身份。
这本书是浦洛基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一本书,他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曾被有意掩盖的真实故事,也因为他的文字,他的担憂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共情。
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事,只会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吗?这是在普洛基完成《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后,被诸多读者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直到这也成为他同样无法停止追问的问题。
四年后,他在《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答案是否定的。
即便技术在进步,安全标准在提升,国际合作在增强,人类的傲慢与失误仍如影随形。核能发展的危险性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无关,它的危险性在于它存在本身。
在今天,浦洛基所思考的不仅是重现过去,还是预警未来。他想要告知公众的信息很简单—核事故还会再次发生,核能发展很危险,而人类目前并没有准备好。
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
南风窗:你对核事故的研究兴趣是否始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这件事的发生,如何影响了你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道路?
浦洛基:首先,我来自乌克兰,这一事故发生在乌克兰,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对我和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产生了影响。
这起事故也对我的学生产生了影响。我的一些学生被招募入伍,并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做清洁工人。那时,军队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而大多数所谓的清扫人也都是军队的人。不过,我的学生们后来又被征召入伍了。此外,我也有朋友去到那里。这是我个人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我一直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实际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尤其是考虑到有关这一事故的原始信息非常有限,因为(苏联)政府在竭力封闭信息。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许多其他人受到事故影响的问题所在。当苏联解体,档案馆开始开放时,我就决定前往档案馆开始这项研究。
南风窗:是什么让你决定开始写《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
浦洛基:《原子与灰烬》是一本我试图回答《切尔诺贝利》读者所提出问题的书。当时,有读者表示,你写了这本书真是太棒了,但你认为只有苏联政府选择不公开信息,并参与掩盖事实吗?其他国家的政府呢?西方的政府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生了六起重大核事故,切尔诺贝利只是其中之一。我的这本书提供了这六起事故的故事,并试图找出什么是共性,又有哪些不同,不仅是在政府责任方面,也在于我们作为人类,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如何应对核能这一全球现象的。这就是我在写这本书时遇到的关键问题。
南风窗:你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描述解释切尔诺贝利事件,你因这本书而构建起来的史学观,是否影响了你对整个人类核灾难史的认知?
浦洛基: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大多来自比较。我学到的一件事是,基本上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来设计反应堆,然后运行反应堆,并专注于此,这在整个领域都很明显,但他们仍然会犯错误。
每次核事故发生后,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整个行业实际上都在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会继续发生重大的核事故,并且每一起核事故的原因都不同,这让我明白,我们能够预测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对人类来说,即便拥有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和最有纪律的人来管理(核电站),由于这一系统太过复杂,核事故还是会发生。这一观点不是我的发明,针对复杂系统,有一个专门类别对此进行研究,有一本书叫《常态性意外》(Normal Accidents)就是关于这个的。
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一条学习曲线,但我对整个行业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我们学了多少,它都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烧水的方式是的如此危险,我们最好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故做好准备。这一结论破坏了将核工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有效途径的普遍信念。
每一次重大核事故,都会对核工业产生全球性的负面影响。虽然福岛核事故发生在日本,但因为这场事故,德国决定无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