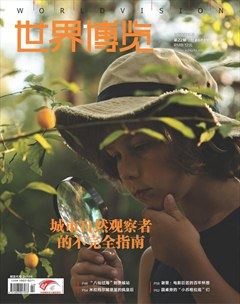那是2022年3月,上海要求居民足不出户的第二周。春天是鸟类求偶和繁衍的季节,途经上海的迁徙鸟类也日渐增多,本是观鸟的最佳时节。可惜这场观鸟者翘首以盼的盛事被猝然打断,彼时我被困在家里,度过最初焦躁无力的几天之后,才终于想起还可以拿起望远镜,看向窗外。
窗外是一片原本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封控后工人撤出,只留下沉默的推土机和高耸的打桩机,几周前喧嚣的园区如今杂草丛生。两个跃动的身影——棕背伯劳就在这时进入了镜头。
我与鸟之间的一条“细线”
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棕背伯劳这个名字,但是对于大部分观鸟者而言,它们是如此常见,以至于被归入了“菜鸟”的行列。名字是相当重要的东西。不少人最初只是好奇于脑海中无意间冒出的那个问题:那只鸟叫什么名字?却最终把观鸟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爱好。
我第一次问出这个问题,是在公园里看见几只蓝黑色和白色相间的鸟儿,胖乎乎地挤成一团。回到家中用图像识别软件才辨认出来是喜鹊。后来我意识到,那对我是里程碑般的时刻:当鸟类之名与形象被连接起来,曾经那个将任何鸟儿都称为“鸟类”的世界不复存在;穿过新世界的单向门,呈现在眼前的每只鸟都拥有自己的中文名和学名,有具体的目科属种,有独特的气质和性格,每一只都与其他不同。

为了避开窗外防盗栏杆的遮挡,有时候我会带上望远镜,在楼道里观察棕背伯劳。熟识的邻居路过,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在看鸟。“怎么看起鸟来了?”他好奇问道。很多朋友听说我在观鸟,也会带着“瞧瞧你这个老年人”的戏谑口吻问我:“鸟有什么好看的?!”
在鸟儿和我之间大概始终有条看不见的细线相连。早在真正开始观鸟之前,我就总喜欢望向天空,遇到美丽的鸟儿,也总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它们一眼,再记录下影像。多年前看《鸟、艺术、人生》,讲一位作家在父亲罹患重病后通过观鸟追寻心灵慰藉的经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看鸟”也可以是个严肃的爱好。
那条冥冥之中的细线真正将我拉近观鸟,是因为我开始构思一篇小说。小说里有个角色是猫头鹰,不知为何,我迫切地想要确定它是什么种类的猫头鹰,才能将故事继续下去。于是我买来一大堆鸟类图鉴,边看边想象哪种猫头鹰的外形、气质和名字更符合角色。我发现,每种鸟儿都有自己多元而复杂的天性,也才注意到鸟类这一庞大群体下不同个体的动人之处。

后来辞了职,我想,为什么不去大自然里观察实实在在的鸟儿呢?于是我来到崇明东滩,开始自己的第一次观鸟经历。站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看风吹过摇曳的芦苇,小天鹅无声掠过暖色的天空和浮光跃金的水面,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观鸟。我愿意独处,喜欢大自然,那根线终于引领我找到了观鸟这个属于我的爱好。
回来后通过鸟类手册和“懂鸟”小程序,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相机里那些鸟儿的名字,鸟类这个笼统的概念散落成了小鸊鷉、白鹭、赤膀鸭、珠颈斑鸠这样具体、细微而美好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