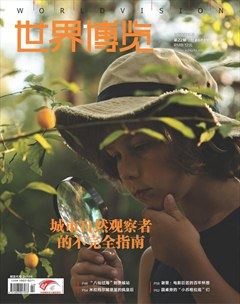在北京观鸟拍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开车奔赴各个观鸟点,扛着机器一直走,不能怕吃苦。北京作为东亚地区候鸟通道交汇较为密集的城市,还有类似北京雨燕这样近乎英雄的明星物种,几乎一年四季都可大饱眼福。只要双腿勤快,“鸟运”自然就有。
我的观鸟初体验
2019年12月1日,我报团去延庆的康西马场观鸟,李思琪是我们的“鸟导”。那年我刚过27岁,人生第一次观鸟,穿土黄色的棉袄,戴着厚帽子,没有长焦镜头,也没有望远镜。那时在鸟类中我最熟的是鸦科,最熟的鸟种是灰喜鹊,做过一些小动物救助。在那辆小巴车上,有两个手持长焦的少年,让我很羡慕。这个时代的孩子能拥有的博物学视野和物质支持是我们初代90后无法匹敌的。在那个冰冻的延庆,我头冻得欲裂,如今感觉不过二字:傻看。
北京刚下过大雪,未经人踏足的郊区,积雪能埋没脚踝,一脚踏进新雪,别提多舒适。在雪后纯净的天气中观鸟,配上一望无际的厚雪,是极其幸福的。而康西马场最为出名的是冬天来此过冬的灰鹤和大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见白头鹤和白枕鹤,甚至是丹顶鹤和蓑羽鹤。
跟团的好处就是有单筒望远镜可以用,在遥远处,一片枯黄芦苇丛边,站着一排休憩的鹤群,由不同灰鹤的小家族构成。经过李老师辨认,其中还有少见的白枕鹤,正在混群休息。在有风和扰流的镜头语言中,灰鹤们也在一种冬日的雪景与云雾缭绕中颤动着,甚至能隐隐听到它们彼此讴哑的呼唤。偶尔有鹤群飞过头顶,人们欢呼着用长焦镜头抓拍,我的热闹就是凑到取景框去,看人家放大的鹤,当时已经很满足,就像冬天时鸟卧在胳膊上,用它40度的体温,熨烫你的皮肤那样感动。

在回去的途中,李老师还惊喜地拍到了在荒野中一闪而过的豹猫,在旁边还有一辆为了拍豹猫而等待救援的私家车。一兽顶十鸟,但那时我离这种欢乐非常远,我刚从媒体离职,稿费要等很久,又没有工作,能看看就不错了。
提到鹤,总能想到卫懿公好鹤。可能他是最早的一位爱鸟君主,最能体会到鹤的灵动与优雅。他给予了鹤无上的荣耀,不仅封鹤为大将军,有食禄。还让鹤坐轩车,导致在狄人来犯的时候,举国的将士们都很生气,“打仗有鹤呢,鹤才享有俸禄和官职,我们去打什么仗呢?!”最后卫懿公还是战败,被狄人分而食之,等到他出使陈国的大臣弘演赶到,发现地上只剩下了一副肝脏,他哭着剖开自己的身体,将懿公的肝放到自己身体中,以自己的身体为棺,随后死去。先不说后代的梅妻鹤子,仅先秦这一段,就为鹤群布下了忧郁的迷雾。

疫情中整装待发
后来,我成了猫盟(以保护中国本土野生猫科动物为使命的民间公益机构)的月捐人,也很快有了稳定的工作。猫盟月捐人的生态发展得很好,可以和自然爱好者们进行各种交流。耳濡目染中,我分期购买了施华洛世奇EL10x32WB的望远镜。
那时工作昼夜混乱,工作因疫情要求严格,城市里到处抓轨迹,我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平时最多不过拿着望远镜沿着颐和园和圆明园走,看到的仅有鸳鸯、绿头鸭、小䴙䴘、黑水鸡、大斑啄木鸟和凤头䴙䴘而已,连颐和园西门繁殖的翠鸟都没时间去看。身怀利刃却无处应用,真是沮丧非常。有去野外徒步的时候,但徒步时间较长,带望远镜好沉。我曾在海拔1000多米的西山中,看到了满山的红胁蓝尾鸲。那辉蓝色的精灵伴着我们一路前行,总飞到我们前面,保持一定距离,侧脸观察我们。我想到了列宁和蜜蜂。不去寂静无人的深山中,永远也感受不到那些小蓝亮片在四周飞舞的感动。王维诗中无限的意象如雪花般涌来,却说不出一个字,只觉得心破裂了小口,汩汩地流出来。
一只被我唤为“黑麦”的北京雨燕是冲破我封闭生活的一小束光芒。每年4月,普通雨燕的北京亚种都会从南非开普敦等地飞回北京进行繁衍生息。它们会遵循这几百年的规律,在北京的北海、正阳门、雍和宫、颐和园等有古代榫卯结构的建筑的地方栖息繁衍,或是去国图、农展馆和立交桥这样的现代建筑中寻找一席之地,展示出了野生动物极大的适应性。初夏,在颐和园的畅观堂,我捡到了一只落地受伤的北京雨燕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