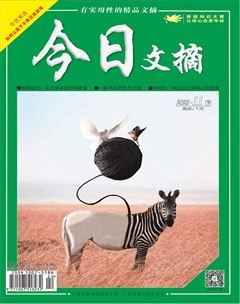炒饭
小时候,蛋炒饭装在搪瓷盆里端上桌。那时我坐着椅子,扒着桌子,鼻尖刚到搪瓷盆边,觉得一大盆蛋炒饭,比山都高。蛋炒饭是我妈的手笔,饭碎粒,蛋成块,金黄泛黑,略带焦香:这是她炒饭的风格,火候唯恐不猛,油炒唯恐不透。我扒拉着饭,稀里哗啦,时不常就一口旁边的汤——热水、酱油、撒点葱,我们那里叫“神仙汤”。我妈炒饭水平并不总是很稳定,但神仙汤总能完美地调整:为炒淡的饭补一点味道,让炒齁了的饭得以下咽。何况只要是新鲜热辣出锅的饭,怎么都不会难吃。如此一口饭一口汤,慢慢地饭吃完了,露出搪瓷盆底的字,标注说那是我妈参加工厂运动会赢的奖品。
于是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蛋炒饭该用搪瓷盆装,搭配着筷子和搪瓷盆轻碰的声音,该是火候猛烈、蛋块焦香,还得配酱油汤。
这个成见,是我上大学时破了的。大一第一学期入冬,到黄昏全身透风,不仅想吃东西,还想吃口热乎的。学校食堂的东西不难吃,但有點像混迹职场多年擅长推诿的老油条,热度半温不火,吃着虚无缥缈,嚼着滑不溜秋,缺少吃东西的实在感。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今日文摘》2023年22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