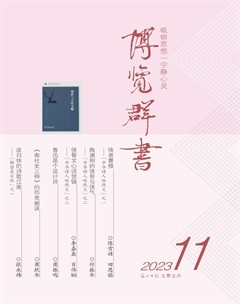贺铸(1051—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北宋中后期著名文人,因其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广受好评,有“贺梅子”的雅称。他诗词兼擅,著作颇丰,有《庆湖遗老集》和《东山词》传世。贺铸为武将之后,性格豪爽强悍,自带“少年侠气”,行侠仗义浸润成人生信条,贯注了其一生。贺铸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侠义品性,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精髓,同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充分体现了侠义精神在宋代经过儒学改造后,增添了“慷慨任气”“率性而为”“忧国忧民”等新的内涵。贺铸自我身世的沉浮多舛,对家国世事的深切关怀,使得贺铸常以侠的行动实践,践履着侠的道德追求,这在他的诗词中多有体现。
诗文皆高、不平则鸣的侠骨文心
贺铸出生于军人家庭,据钟振振《贺铸年谱简编》记载,贺铸的六代祖为五代后晋的贺景思,他曾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共事,高祖、曾祖、祖父都为朝廷武职。20岁时贺铸由门荫进入仕途,担任武职。在贺铸所生活的宋代,朝廷和民间都倾向于重文轻武。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教训,采纳了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通过“杯酒释兵权”从武将手中收回兵权,实现了朝廷对中央禁军的控制。太宗时期,由于对辽战事的失利,北宋的军事策略由“进取”转为“内缩”,太宗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便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便被宋朝历代统治者沿用。北宋整个社会对武职抱有片面的歧视,武人处处受到压制,庙堂实际上成了文人掌权的政治。宋人蔡襄曾感叹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吴以宁点校《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二二,P384)
渴望建功立业的贺铸不满足自己一介武夫的身份,他在习武之余,也潜心研习六艺。贺铸的好友程俱称贺铸“然遇空无有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潜心治学、昼夜苦读的贺铸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宋史·艺文志》记载贺铸“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李清臣在举荐贺铸转官的奏章里赞赏贺铸“老于文學,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陆游《老学庵笔记》称赞贺铸“诗文皆高,不独长短句”。当自身特质与宋代整体的文化环境产生差距和矛盾时,贺铸尝试去改变自己,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以期满足社会期待,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故而在贺铸身上,既有豪气慷慨的侠士之风,又有勤学苦读的文人丹心,可以说,优秀的文化素养,是贺铸驱遣文字书写侠义精神的必要前提。
贺铸性格秉直,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要发出不满的呐喊,并用文字释放他胸中块垒。这在他的《行路难》中有直观的体现: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前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行路难》是乐府旧题,文人经常用此题来抒发壮志难酬之感。贺铸也用此题来表现自己仕途不顺、落拓不得志之感。贺铸20岁由门荫入仕,授右班殿直,直至其40岁,二十年间一直在武官系统里磨勘迁转。他担任的差遣多是监酒税、监都作院、宝丰监、巡检等职务,官品既低,升迁又难,所任的差遣又繁杂费力。自开国以来,宋代统治者就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政策来拉拢知识分子,加强中央集权,武官在宋代的地位直线下降,贺铸一直有改武为文的念头。元祐七年(1092),在李清臣、苏轼、范百禄等人的推荐下,贺铸由武官转为文官,但贺铸并没有因改为文官而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此词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二年(1108)之间,贺铸在泗州、太平州担任通判一职。这时的贺铸已过艾服之年,距离改为文官也过了十余年,但贺铸担任的仍是通判这一低微的官职,辗转各地、屡仕不进的仕宦经历使得贺铸内心无比的忧愁苦闷。
此词上片直抒自己的愤懑不平。“缚虎手”,借指力能缚虎,有军事才能的人;“悬河口”,指口若悬河,有政治才能的人。这样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人理应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可现实中却落得个“车如鸡栖马如狗”的悲惨处境:人才只能跻身在像鸡一样窄小逼仄的马车里,拉车的马像老弱不堪的瘦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