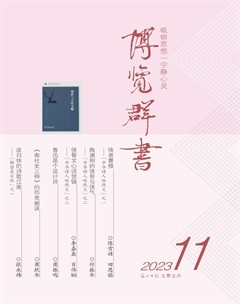晚唐文人皮日休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接过韩愈“文以载道”的理论旗帜,推举儒家圣人之道,强调文学的美刺、教化之用,于一片颓靡之音中,爆发出时代的强音。他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文中极赞韩文:“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系公之力也。”皮日休之所以如此推举韩愈,正是因为韩愈之文担负起了传播儒家圣人治世之道的重任,其中,“裨造化,补时政”的儒家功用主义文学观正是皮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故其在《皮子文薮》序中强调此十卷诗文“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关切社会民生
皮日休心系民瘼,诗兴亦多因民生疾苦而发。他在《正乐府十篇》之序亦云:
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
皮日休将所作十篇乐府诗称之为“正乐府”,即是取拨乱反正之意,企图以此恢复诗歌观百姓民生与察政治得失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皮日休的《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
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
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
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
少者任所归,老者无所携。
况当札瘥年,米粒如琼瑰。
累累作饿殍,见之心若摧。
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尘埃。
其命即用矣,其赏安在哉?
岂无黔敖恩,救此穷饿骸。
谁知白屋士,念此翻欸欸。
此诗将叙写视角聚焦在“卒妻”这一特定的身份上。作为戍卒之妻,她既要承受丈夫因戍边而不幸离世的痛苦,还要在家徒四壁的困境中艰难存活。然而,时疫肆虐,又逢荒年,百姓饥馑,饿殍遍地。作为戍卒遗孀,卒妻不仅没有受到朝廷的半分恩赏与优待,反而落得身委尘埃的悲惨结局。皮日休通过“卒妻”这一小人物铺开描写的宽度与广度,将戍卒之苦、卒妻之哀、荒年之难、人命之轻纳入笔下,客观而又真实地再现了晚唐时期民生凋敝的惨状。
皮日休还选择了“橡媪”“陇民”“农父”等具有特定身份的下层人物,全方位展示社会苦难。《橡媪叹》中的黄发媪虽然“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但因田税苛重与狡吏勒索,只得在荒芜山岗捡拾橡子以充饥肠。《哀陇民》中,蚩蚩陇民為满足上层社会玩赏鹦鹉的爱好,被迫登上万仞之高的陇山之巅,却落得“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的凄惨下场,可见陇民生活之艰苦、生存之艰难。《农父谣》则以农父这一底层人物为切入点,以其“农父”之口亲述遭遇感慨,笔锋越发直接、犀利。农父冤辛苦,向世人述其情:
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
如何江淮粟,挽漕输咸京?
黄河水如电,一半沉与倾。
均输利其事,职司安敢评!
三川岂不农?三辅岂不耕?
奚不车其粟,用以供天兵?
此诗叙议结合,以农父之口陈述农事之艰难,其不述躬耕之苦,而是将矛头对准了京师对农民的盘剥与掠夺。不合理的运输方式,掌管物资运输官员的以权谋私,以及舍近求远的征粮政策,加重了江南地区农民的负担。漕运伤民,恶性循环,农父苦不堪言。
皮日休对民生疾苦感受颇深,在诗歌中还毫不避讳地提及官吏凶狠、贪婪的丑态,如《贪官怨》:
国家省闼吏,赏之皆与位。
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
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
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箠。
吾闻古圣王,天下无遗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义。国家选贤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禄位。何不广取人?何不广历试?
下位既贤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赏以财,俊造悉为吏。
天下若不平,吾当甘弃市!
因朝廷在选拔人才之时,未以“仁义”之士为先,又对所择官吏不加束缚,以致所选“人才”不通诗书,不精吏治,愚蠢者对生民之苦视而不见,狠毒者残害百姓不知收敛,无辜百姓因此受难。面对朝廷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后患,皮日休提出“广取人”“广历试”的建议,企图冲破当权者以门荫或裙带关系垄断科举,致使贤良之士难以入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