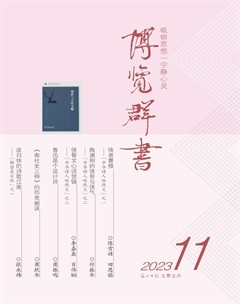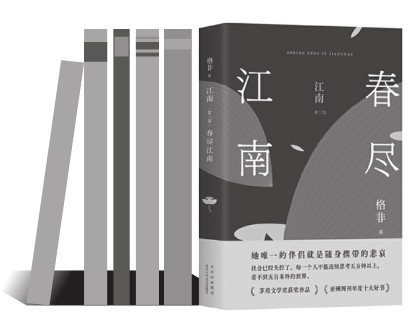
格非在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及《春尽江南》),是少有的刻画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社会转型中,青年心灵动荡与价值重塑的重要作品。其中第三部《春尽江南》(《江南:(全3册)》,格非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谭端午在经历政治风波后避居家乡鹤浦,并与妻子家玉(最初相遇时叫秀蓉,后改名)重逢结婚。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环境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氛大有不同,变得更加速食和功利化,这使得端午的内心变得极为焦虑、抗拒和痛苦。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其妻子家玉,家玉积极地改变自己原来的诗歌理想,转向功利化的生活之中,改行做了律师,并成了一个逼迫孩子学习的母亲。然而家玉顺应时代的努力并没能使得她过上舒心的日子。在自己付出了心血的房子被人强占,而利用法律手段无门,反而是通过黑道人士解决了问题后,家玉对社会现实已经感到深深的失望,进而陷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之中。而反观端午,他则早已对社会失望,并致力于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后来,家玉因患癌症住进医院,她也终于放下对名利的追求,回归心灵,重新拾起诗集,变回了最初与端午认识时的“秀蓉”。夫妻两人的关系重归于好。但这时秀蓉已然病重,最终独自一人在医院逝世。而端午也不再逃避自己内心的冲动,开始创作小说。两个主要人物都寻回了内心的归宿。
作者十分关注在价值变幻的时代中无助彷徨的个人,甚至把这一视角定位为文学写作的价值之一:“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而正是失败者才肩负着反思的任务。”《春尽江南》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心怀盼望却终日不得志的端午、被现实打击得了心病,而始终怀有内心一片净土的家玉不都是所谓的世俗“失败者”吗?但是,这些人的心灵被格非的笔触、被文学照亮了。《春尽江南》既是一部社会转型的反思录,又是时代下人民群像的心灵史。
生存困境与诗性叙事
在格非个人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学的邀约》中,提到关于中国传统叙事方法,对抒情性与叙事性交织的特点有详尽的论述。而他本人的作品也浸透了诗性叙事的特点,可谓是情景交融。这一特点也称作“叙事情境化”,所谓“歌文杂陈,韵散交织,叙事与抒情并重”,非常具有感人的力量。格非在分析《源氏物语》时,还进一步认为作者笔下的叙事其实都是笔下人物情感的投射,皆为抒情。他在访谈中响应十年后的作品转型时,提到自己30多岁重新开始研读中国的传统文学、古典叙事作品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另外,小说诗性特征浓厚的废名也对格非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格非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废名的小说,可谓是用力颇深。
《春尽江南》利用诗性叙事来叙述主人公端午和家玉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过去,他们一个是对社会改革有热血冲动的青年诗人,一位是纯真且对爱情、诗歌有憧憬的女大学生,在充满诗意与感伤氛围的招隐寺相遇了,而对两人90年代重逢后的描写,格非的笔下则充满着现实主义机锋的讽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往往伴随着诗意的陨落与心靈的荡失。而作者格非并没有一味地进行肤浅的诗意呼唤。他虽然对当下的物质追逐的局面并不趋附,但也对“理想”“革命”等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文中无数理想主义者向往的花家舍总是充满着悖论性的展现。在第一部《人面桃花》描述的民国时期,花家舍既是土匪窝,又是文人王观澄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地方。而到了《春尽江南》,花家舍一面是举办诗歌大会的会场,一面又是暗藏着情色交易的场所。
确实,现实的这样种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巧合地共存了。这不由得让生存其中的人们也体会着这种内心撕扯的感觉。没有人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实现理想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与欲望调和与共处的过程。但最终勇敢的诗人会冲出现实的迷障,回归心灵的平静,这是作者想要表现的主旨。因此,诗性叙事交织着现实主义叙事,人物的理想、道德抉择与现实压力等形成了书中最迷人的张力,也回答了“诗人何处去”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