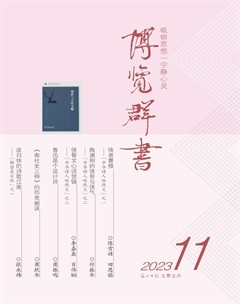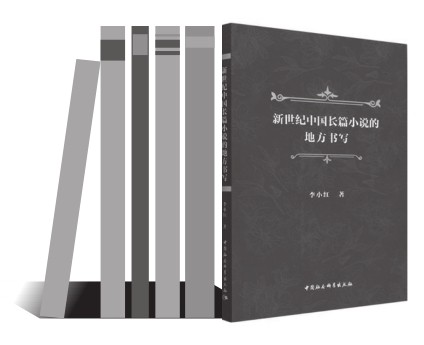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疾席卷社会各个领域,文化全球化随之也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但是,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理解和应对,呈现出多种取向: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文化的形成,可称之为文化同质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从文化全球化的实际进程来看,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未能全部转入全球文化同一化的轨道,相反在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相应的呈现出抵制与抗拒的姿态,这就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不悖的过程,在此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双向互动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就会发现新的历史时段中的文学重新发现了“地方”的价值,试图在地方气质和精神的勘查和挖掘中,找到文化全球化时代中本土化的地方路径。
《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地方书写》是李小红博士的第二本专著。她的第一本著作是她的博士论文结集而成,主要研究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可以说是她在长篇小说研究领域继续深耕的结果,作者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中,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敏锐而恰切的判断,选择从地方书写的角度探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质素和样貌。尽管这一分析和研判多为个人所见,但大致可以窥视到新世纪长篇小说发展的整体面貌。
对于文学与时空关系的研究,中国历来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刘勰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来说明了文学与时间的关系。然而,文学的发展不仅与时间相关,它与具体的地域空间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文學话语的生成总是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离开了具体的时间、空间,文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文学对于空间,不仅是被动的反映,文学对空间有着形塑的作用。因此,特定的文学话语,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会产生,文学总是一定时间、空间的再现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与时空的关系,有不少充满真知灼见的论述。比如《隋书·文学传序》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有“北方之地,上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地理大势论》的论述则更为较详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
可见,文学不仅影响到文学的主题的表达,题材的选择,对于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在国外,20世纪7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下,人文社会学科掀起了空间与地方研究的热潮。文学地理学的诞生,就是在文学与地理之间架起了跨学科的桥梁,文学与地理的融合,并不仅仅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在文学再现过程中记述和延续地方的文化记忆,保护并传承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