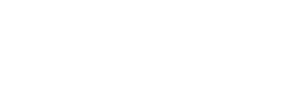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名字称呼你?我完全不知道。当战争中被称作海德的人,在战败后失踪,然后又以杰科博士之名重新出场,可见事态已极为明了。我要爽快地称你为亨利·杰科。但是,你的情况却更为复杂。杰科确实出现了,但爱德华·海德也并没有消失。你现在仍然用海德的名字,积极发表意见。只不过是用着与杰科相似的口吻。反战论者杰科博士大肆夸耀自己的卓见,而战犯海德则忙于自我批判。

这段内容出自日本著名评论家花田清辉1946年所写的一篇短评《杰科与海德》(刊载于《真善美》1946年8月号,最初发表时并无题目),他借用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人公—杰科博士及其另一重性格的化身海德,将日本战败前后知识人身上所展现的“双重人格性”批判得淋漓尽致。不过,花田的笔锋并非仅仅指向那些欺骗并煽动民众投身于战争的知识人,负有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也在其批判行列。花田在文章末尾这样写道:“问题在于,你身体中的杰科和海德并没有展开激烈的斗争。杰科博士哟,你要是制作战犯名单的话,要把海德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那时,你会切身体会到,努力不做伪善者,是多么辛苦的事啊。”
如果以日本本国文明与历史发展轴线来重新审视近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天皇及天皇制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主题,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思想的中心命题。自明治维新以降,天皇制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凝聚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装置,而在天皇制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也为日本人区别于“他者”提供了内在的立足点。在神权天皇观的灌输下,日本国民直到日本战败投降,都将天皇视作最高的献身对象。然而,在“大东亚战争”开战诏书上捺印的最高责任者却逃脱了审判,被占领军重新置于民主国家的中心。当军国日本摇身一变为民主国家,天皇的地位及其权限也由“元首”转变为“象征”。对于战后的日本精英阶层而言,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性资源唯有诉诸天皇才感觉最为妥当。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田庆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认同》)一书,为我们了解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在确立“自我”主体性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不仅如此,该著在对日本精英阶层利用本土资源建构国家认同的内在理路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一种“他者”视角,对战后日本内外思想资源的纷繁复杂态势予以条分缕析,揭示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所蕴含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厘清了日本传统本土思想与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思想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问题。
《认同》绪论指出,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形塑的国内外资源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学理探讨,从而深刻剖析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泛滥的思想根源。众所周知,“和平国家”“民主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宪法第九条”,乃是战后初期日本受到各方面条件制约而被动或主动选择的产物,这本是战后日本整合国民认同以及面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形象的主要资本,为何日本政治家要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颇具国家软实力的充满正能量的“国际形象”进行解构呢?实际上《认同》试图回答的问题也在于此,即对于“民主国家”的国民而言,认同国家的民主理念本身是理所当然之事,且是列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依据,那么为何还要依托天皇制重建战后日本的价值体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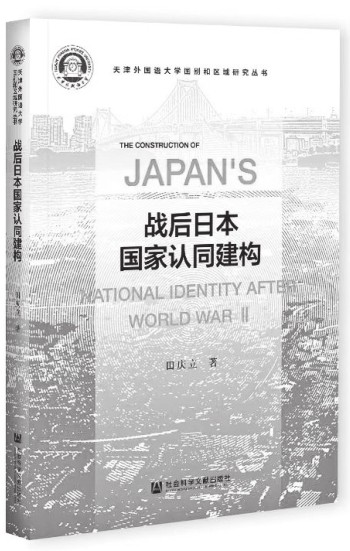
从《认同》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以天皇、美国和中国因素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主轴,讨论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本土资源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资源,自内而外地界定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向度,即“求同”与“斥异”的双重向度。这里的“求同”是指日本“继承、发掘及革新”既有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天皇制,通过象征天皇制增强国民面向国家的“凝聚性认同”,重塑和强化政治的合法性,进而维系国民的一体感。而日本在面对与自己相异的“他者”时,或是出于利益驱使而“形影相随”,或是由于价值判别而“敬而远之”。在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美国充当了“价值标准”的角色,“基于美国国家超强实力的吸引,日美安保体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以及日本国民的亲美情结”,作为“他者”的美国发挥着强化“合作性认同”的效能。在《认同》一书的论述框架中,战后日本国家认同从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护持国体”,逐步向以日美同盟体制为核心的“新国体”演进,并由此形成了“对美从属”的构造。这不仅促使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摆荡于“亲美”与“反美”之间,还使战后日本的国家建构陷入两难之境。另一方面,“斥异”体现为想象和寻求对立的“他者”,通过确立本民族国家的“对立者”和“假想敌”的方式,有意识地利用和倚重民族主义的力量从外部强化国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