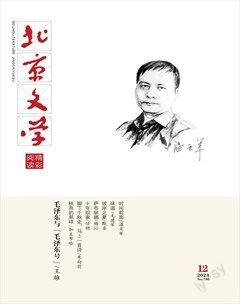青春与暮年几乎遥不可及。青春为了自身的利益,本能地回避暮年;暮年追怀青春,但只能以一种隔世的方式。因此,青年作家较少涉入老年题材,偶尔涉入,也多以一种外部的方式,很少窥入老年生活的内面;老作家反过来,并不避讳青春的题材,但却鲜能表现出真正的青春热情,一旦成功,就要被目为奇迹,成为老年的骄傲。
这部《十年织家》是一个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处理的却是老年的题材。小说写一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老夫妇去世前最后两年的生活,细致地写出了他们生活的困顿和内心的纠结。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作者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仅凭文风推断,你大概会以为是个老作家,或至少是成熟的中年作家。这种反差大约是作者有意为自己设置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有关于经验,需要作者突破青春经验的局限,去表现自己完全陌生的老年经验;另一方面有关于形式,需要作者在青春阶段提前发明一种老成的风格。小说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说对老人生活和心理的表现准确细腻,小说的风格也显示出一种与题材一致的老成、稳重和扎实。这种老成不仅表现在遣词造句上,也表现在叙述的语调和节奏上。这是很大的成功。我有一个看法,在作品效果一定的前提下,作家的才能与题材的难度成正比。但题材的难度并无统一标准,对甲作家难的,对乙作家可能轻车熟路。不过在一般情形下,题材的难度可以用作者和题材的距离近似地代替。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作家的才能=作品的效果×作者与题材的距离。我认为,这个公式在小说中成立,在诗中同样成立。由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推知这个作者才能的富有。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想象的才能。我们一般把想象和虚构、幻想、非现实联系在一起,与一种远离实际经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很少会把它与真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会说屈原、李白富有想象,会说《封神演义》充满幻想,也会说《西游记》想象瑰丽,但很少有人说《金瓶梅》的想象,《红楼梦》的想象(撇去其神道设教的成分)。后者被我们视为现实主义的。我们通常认为现实主义基于作者自身的经验,或者顶多与一种精密的观察力有关。其实,任何真实都离不开想象,也可以说我们所谓的现实就是想象的创造。在这一点上,米沃什的意见值得注意。在《猎人的一年》里,他曾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德莱塞的《美国》是“伟大的幻想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十年织家》也是一部想象生动的作品,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想象、现实、现实主义的关系,正如《红楼梦》或《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