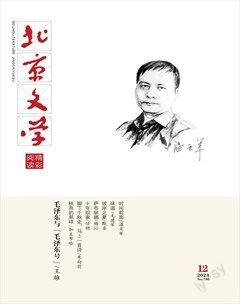惊天二问动天下——《沁园春·长沙》
这是1925年秋天,32岁的毛泽东即将奔赴广东去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际,故地重游,追往思来,感慨良多,诗兴大发,一挥而就。这时的毛泽东正处于从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向武装革命的实践者和领导者转变的过渡期。虽然此前毛泽东在组织领导湖南学生“驱张运动”、成立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诸事上都成绩斐然,但要说真正的武装斗争,还得是整整两年以后即1927年的秋收起义。所以,词中还保留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同时,又是毛泽东告别书生意气、问鼎天下的青春宣言,初步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代诗人的基本特点——气势磅礴,想象浪漫,文辞华美。
譬如“文辞华美”吧。开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即使人联想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光昌流丽和奇谲想象与意境辽阔——“洞庭波兮木叶下”的那种寂寥、邈远、萧瑟感扑面而来。同时又有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伟岸的孤独感。接下来笔锋一转,“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色彩绚烂,文辞斑斓,生机盎然,又流露出青年毛泽东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仰观俯察,细致入微,以至于一鸟一鱼,都历历在目,又令人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中之名句:“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盡精微,致广大,显示了诗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深厚浸润。
再譬如“气势磅礴”——仅“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口气用了三个“万”字,大气逼人,不仅不觉堆砌,更无病态,反倒觉得珠玉流转,层叠回环,气势雄霸。更厉害的还是上下阕结束的两问。
上阕问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石破天惊,犹如屈原之“天问”,更像骆宾王的檄文之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正像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所写的社论《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大家想想,此时的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一介布衣,虽说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执委,但那时中共弱小,尚未执政,实际的具体工作是回韶山建立党支部,职务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村支书;同时他自己还正遭到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通缉,有生命危险。可是毛泽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天下为己任,问鼎天下,舍我其谁?可以说,此中足见青年毛泽东三大精神特质:一是志向远大的雄心壮志;二是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三是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此三点可视为毛泽东一生的成功秘诀,也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遗产,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年人学习。
然后就是下阕,“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注意,特别是全诗的最后一问:“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又是一问,且直抵要害。此问也有两解:一解是,问罗章龙、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等同学少年、三湘才俊,还记得吗?当年为了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磨其心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湘江游泳击起的浪花阻遏了飞驶的行船。二解是,还记得当年我们的约定吗?相约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投身时代的洪流之中,掀起滔天的革命巨浪,打翻旧中国那艘即将沉没的破船!现在时候到了,毛泽东即将去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要培养农民运动的火种,撒向全国,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4年后,毛泽东领航的新中国的航船驶出了东方的地平线!真个是:热血唱响《沁园春》,惊天二问动天下。
如果说《沁园春·雪》,是中年毛泽东完胜天下的胜利预言;那么,《沁园春·长沙》就是青年毛泽东问鼎天下的豪迈宣言。
推敲了一年的48个字——《十六字令三首》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历史上的《十六字令》就缺少名篇。为何?因为它的形制过于短小,它就是最小的小令,《十六字令》就是16个字(著名小令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还28个字呢),还没开头就已经结束了,此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写的: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虽然短小,但口语生动,描绘传神,无论言其高,言其雄,言其险,都有一股大气磅礴于其间,毛泽东诗词的全部特点都浓缩于此。
显而易见,《十六字令三首》中的山不是“我见青山多妩媚”式的思念,也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自然复现,而是经过了诗人艺术想象、提炼与升华的山。它之所以非写某地某山,因为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体验赣、湘、黔、滇、川、陕无数奇峰莽岭之后,再酝酿、构思、修改和润色而成,故作者自署创作时间为“1934年到1935年”,完全真实地反映了创作的实际情况。
第一首写的是山的崔嵬和险峻。长征其实就是大范围的转移,前有崇山峻岭,后有快马追兵,这就促使部队常常是策马加鞭仓促行进。每当毛泽东登上高峰回望来路时,都蓦然惊觉,几乎头顶苍穹,手揽流云,不禁倒吸一口气:“离天三尺三!”
第二首写的是山的雄浑气势。本来山是静止不动的,最多是山上风大时,草木会随之摇摆,而由于毛泽东本身是行动的,他观察的角度也是动态的,或许他还是骑在那匹大白马上。那么山在他的眼里就可以像江海那样翻腾起波浪来,而他本身也在这种波涛当中,他觉得山势实在是太磅礴了,在奔腾,在怒吼,在旋转,甚至在跳跃和倾倒。于是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伟岸的群山就好像干军万马厮杀正狠。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恢宏且尖锐。由险到雄再到锐,气势更烈,意象也更加犀利。如果说第一首里的山是“离天三尺三”,还有“三尺三”的距离的话,那么这首词里的山更是好像枪和戟一样直接刺破了青天,甚至成了天地赖以存在的中介,没有山支撑的话,天就会坠落下来。这是一幅难以描摹而又宛若目前的画面,诗人主观色彩浓厚,极好地展现了毛泽东雄奇大胆的想象。
三首词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写的是山,但是通过对山的描写,却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干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和毛泽东自身的博大胸怀、宏伟抱负和超凡品格融为一体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再留意一下此篇的创作时间——“1934年到1935年”。也就是说《十六字令三首》48个字,毛泽东在马背上推敲了一年,或者说至少跨了两个年头。那时候,虽然常常天上有飞机,后面有追兵,凶险万状,莫此为甚。但是,其一,长征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毕竟是打的时间少,走的时间多,毛泽东常常骑在马上摇头晃脑,吟咏推敲。20年后,他竟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毛泽东自称“马背诗人”,即由此而来。其二,当是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毛泽东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同时又是马背诗人,他似乎完全将自己置身事外,以郊寒岛瘦的苦吟精神来苦苦追求48个字的最佳效果。这种身份的反差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的奇妙组合,也成了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个结尾,超过了李白——《忆秦娥·娄山关》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他非常看重这首词,曾经把郭沫若《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中关于这一首的解释全部删除,然后以郭老的口吻,为郭老操刀重写一段。从他自己的解释来看,《忆秦娥》作于1935年2月底重新攻占娄山关之后,并不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次攻占娄山关时。从1月份的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核心,逐渐恢复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正所谓受命于危难之际,能否挽狂澜于既倒?
纵观毛泽东诗词,其风格一贯高亢激越,其心情从来阳光健康,而且越遇到挑战越是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