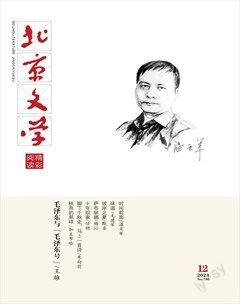残橘
上世纪末,雪燕老师从美国回来时,告诉我,美国有许多果园都没人采收,果子烂在园里,还得请人清理,让汽车拉走,当垃圾处理。我当时不解,那是证明美国鬼子兴旺,还是证明美国鬼子没落呢?现在,我亲眼看见一园过熟橘子,落在地里烂掉,我才晓得橘市弄人,有几许庭院深深之意。这与兴旺和没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记得从前我们在荷池上赏花,剥莲蓬,兴致高时还对起句来。一个说“归期莲池岸,我自日边来”,另一个就说“伊从阡陌下,告我千日红”;一个说“两峰藏云雾,一柱犹挺拔”,另一个就对“荷叶田田映,舒卷自在开”。闹腾着,并推敲着字句,有些许文艺,也有些许放荡,就像敬亭山里面的暧昧。脚步所至之处,虫声就停了,只听得荷田里水声咕嘟,鱼蟹戏逐。那时斜阳在山,穹庐如盖,千日红在陌上灿烂着,是阳光铺下的一条地毯。那个归期的“日边来”,却又分不清是清晨或黄昏……
后来夏天逝去,天空和大地的色彩渐渐深浓。荷花谢了,莲蓬干了,莲叶耷拉着,枯卷。我们就移步向橘园。一条工作便道顺着山腰走,穿过丘陵坡地,橘子结得多好哇,千树万树张灯结彩,满满的望头无边无际。驾着车子驶过,橘灯晃眼,一路留香;把车停下,走一程吧,橘子就会擦着眉眼,摇晃着。晴日闪着金光,雨过吊着露珠,只待秋来催熟。
他们见多识广。他们能分清橘园中的繁多品种,能细说那些品种的根底和来龙去脉,仿佛一个个族群的起源、发展、迁徙、变异,并且描摹出它们的酸甜口味。比如蜜橘的津甜,金橘的甜中带着扑鼻的柑味,久久留香,椪柑掰开时喷得满手的橘汁。我分不清那些品种,就像分不清街市中的人群,男男女女红红绿绿,白天华服美食,夜晚不知所终。可是,人与橘可以同比吗?不能。人可以装,装傻装古装帝王装叫花子无所不能,而橘不可装,由绿变黄,由酸变甜,全然任季节装点,毫无伪饰粉饰。所以他们对橘的评头论足,可信度自然很高,而鲜衣怒马之人,谁知道包裹着什么灵魂?
我乱七八糟地联想时,橘园下,果农间作的葱蒜、蚕豆,也都绿汪汪的,正牵着我的思绪。霎时,那种餐桌上的美味又把人勾住了。灌园的水渠边,各种野生植物也蓬勃生长着。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刚刚认识的叫水蜡烛的植物,它们成排成簇,举着暗红色的蜡棒,油亮亮的,像在燃烧。还有刚刚抽穗的马儿秆,含苞的野菊花、千里光,都在流水潺潺中摇曳。从此,橘园就成了我们的乐园。
曾几何时,水蜡烛过早地枯了,油润的暗红变得暗黑无光。野菊花和千里光怒放,星星点点满目金黄。橘子熟了。我们沿着小路走去,果农忙着采收。我们一路地尝去,蜜橘、金橘、椪柑,然后将手捂在鼻上,细细闻香。苏东坡写吴地的橘香是“吴姬三日手犹香”。现在,以我们黔地的经验来看,那是真实可信的。只是,如今橘价的烂贱,却可能是苏东坡难以想象的罢了。
今天,我们又走进橘园时,果农已经不再采收橘子了。一片片的橘林里落满橘子,树上过熟的残橘经了霜雪,甜似糖蜜,却再也无人问津。几个果农正在橘园中剪枝,他们沉默不语,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沮丧。也许有,在他们心里。我猜想,他们如此精心地剪枝呵护,一定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来年吧!我爬上园子,摘下了半桶残橘。剥开来时,过熟的橘子已掰不开瓣。整个儿地放入口中,津甜入心,一路留香。
这蜜甜的残橘,也是庚子年的馈赠!
病室陪榻录
昔時读韩愈《祭十二郎文》,始知十二郎因病足而卧,直至终殒。然病足之苦,却恐非患者不可深悟,其痛难当。就如读《祭十二郎文》,关注其文常甚于病足,念惦韩愈亦甚于十二郎,盖因读者未罹病足之故也。
父亲今岁八十有四,身体向来健朗,未知医为何业,药为甚物。许是因年壮时过度劳顿,至晚年患上足疾,往往而剧。做医生的二弟便时时告假,带些药物器具,为父疗足。我则放浪形骸,忘情于江湖,不知父亲之病苦,二弟之忙碌。好一个行空天马。今细细思量,惭愧得很!
我与二弟幼时耕读,及后离家,混迹于江湖,奔走于衣食。父亲便与三弟居,虽时有龃龉,却幼爱老孝,已数十年了。自三弟当兵吃粮回乡,原也想谋一份官活,混其粮饷,以了卒一生。初,应聘于镇计生部门当差,效犬马之劳,隳突于乡野村落,不久便觉有悖心念,烦不胜烦。于是自知不宜于此偷生,便断然放弃,回家种地,纵情于土地河山,娶妻生子,日子庸庸常常而过。后来随打工潮的泛起,也弃乡而走,常年在外,皆为稻粱而谋。父亲和侄子女们便成了留守老人和孩子,隔代相依,聊聊以期卒岁,兀兀以待穷年。
初时,父亲足疾轻微。每次肿痛一阵,过后就好了。我们都不在意,以为乡村之人,耕田犁地,风吹雨淋,微小脚疾不足挂齿,服些二弟开去的药,不久而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