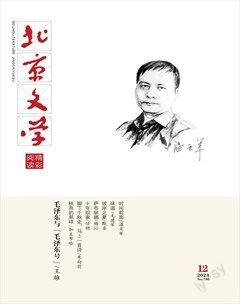由《周庄水韵》而生发的关于周庄的想象,今天终于走了一遍。在想象与现实中独游,古镇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微妙,宛若一首并非全然合辙的诗歌,总在某个拐角忽地涌现另一番景象。
大约中午才起床的,醒来推窗,阳光明媚,就打算出游。转了三趟车,拐了许多小巷,目光游离于那些白墙黛瓦之间时,偶见一位老人蹒跚而过,消失在与我相左的巷口。脚印恰始残留些记忆,一阵风就从瓦缝袭来,卷走那些悠然的目光。再用新的目光追寻逝去的自我,则听见一阵孩童的欢声笑语,消失在目光的尽头。
又空巷。
而后渐闻人聲水声迭起,过了小桥,古镇的入口赫然在目。
天光占领了整个大地的时候,则大地全是烈阳。从宽阔的入口进入古镇,左右可见许多小店,有供应茶水的,有摆卖布料的,大都寻常可见,不过是处在古镇之中,借了古镇的光,做了古朴的样子。
初见周庄,心中是有些失落的。读《周庄水韵》,看江南古镇的绘画,总觉得它该如水墨一般,清静、淡雅,每每使人陶然忘机,心旷神怡。但当我真正见了它,却有些后悔作出出游的决定,也有些后悔相信作家和画家的笔墨了。
从入口直行,见一墙,右转,而后左转,能够看到一面更大的墙。墙上有展示周庄生活的浮雕,其后是一条小河,小船摇曳,在树影中款款向前。如果摒弃周遭的喧嚣,只留船桨划水声,间或传来头顶鸟鸣声,合上船头妇人擦汗的举动,乘船人欠着身子指向河岸,小船晃晃悠悠地钻进桥洞,两岸是行人,是看船的人,是轻摇蒲扇的白发人……
想来是带着美妙的。
沿河而南,有周庄博物馆、周庄博物馆文创和一两家餐饮住宿的店,过店东折,上小桥,再于炎炎烈日中左右观望,也实在不能感动于它。
而后又穿越了许多巷子,在一家店里吃了午饭,带着对苏州饮食一贯的嫌恶继续向前。在所谓“砖瓦窑”的地方看了些砖,也看了瓦,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瓦窑。儿时常听父亲说,家中的瓦全是祖父烧制的。
“哪儿烧的嘞?”我问。
“瓦窑。”
“怎么烧的嘞?”我又问。
“不晓得。”
父亲晓得祖父在瓦窑烧瓦,也晓得瓦窑在一处罗姓人家的屋边,却没有见过瓦窑,当然不晓得烧瓦的工艺。这多少有些遗憾,毕竟对于挚爱“怀古”的我来说,亲见瓦窑是极其诱惑的。然而那罗姓人家的屋边只剩一堆黄土,不见半点瓦窑的踪迹。十多年的夙愿在今日得以实现,也算是极大的补偿了。
我仿佛产生了别样的兴味,有别于印证关于周庄的想象的兴味。
从“砖瓦窑”出来,正要穿过小巷,却被一家玩具店给勾住了。那老板只管拿着一个飞天的小玩具叫卖,让我买一个回家,给孩子玩儿。我自然不快,我原是打算给自己买的。刚要走,转身之际,却看见一只木蜻蜓,小嘴尖在一小棍上,身体悬空,却总摇晃不落。那摇曳的姿势也过于逼真了些,将我也动摇得无法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