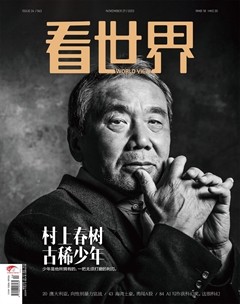曾经的独角兽企业、“共享办公”的鼻祖WeWork,终于没能扛过新冠疫情的冲击,迎来了破产的结局。
11月6日,WeWork向美国新泽西州的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退出在北美各地的60多份办公室租赁合约。WeWork表示,这是公司“全面重组”的一部分,约92%的债权人已经同意将债权转换为股权,进而削减约30亿美元的债务,以此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
曾经,在热钱汹涌的年代,WeWork乘着“共享经济”的东风,迅速崛起为全球性巨头,直至在150个城市拥有850多家门店和超过100万个的工位—尽管从未真正盈利,但在风险投资的不断输血下,WeWork的估值还是屡创新高,一度高达470亿美元。
然而,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方式的改变,对这家“共享办公”巨头造成了深刻冲击。彼时,风险投资的热潮已过,缺少盈利手段的WeWork在失去风投的输血后,很快被沉重的债务拖垮,最终走向破产重组。
WeWork的破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投资狂热时代的失败案例,而且也意味着“共享办公”,这个秉持着开放与分享精神的商业模式,来到了一个需要重估与反思的时刻。
一场泡沫
尽管WeWork是“共享办公”行业中最为耀眼的一家企业,但“WeWork的商业模式称得上共享办公吗?”这一问题,却一直伴随着WeWork从崛起、兴盛到最后衰败的全过程。
“共享经济”这一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对闲置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然而,以“共享办公”先驱者面貌出现的WeWork,一直饱受商业模式上的质疑,与其说它是“共享办公”,不如说更像是“二房东”。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趁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在纽约包下了一些闲置写字楼,对其进行简单隔断后,出租给一些小公司,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二房东”生意。
后来的WeWork在商业模式上与其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仍然是向写字楼租赁楼层,改造成共享办公空间后,转租给企业或个人,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时尚装潢、免费啤酒等看起来很“酷”的元素。
但是,当这个分租的生意,披上了“共享经济”的外壳后,看起来很新潮的共享办公室,便在资本层面拥有了一个好的故事,在此前风投兴盛、遍地热钱的时代,引来了众多风投涌入。
本质上是“二房东”的生意,想要实现“万亿市值”是多么不切实际。

当中,孙正义的软银集团是其最大的投资者。据说,孙正义仅在与诺伊曼同乘一辆车的12分钟内,就敲定了对WeWork超过40亿美元的投资,他还为WeWork定下了比诺伊曼的“千亿”规划更为宏伟的蓝图—成为万亿市值的巨无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