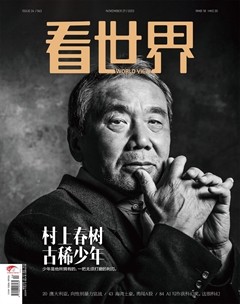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成为近20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巴以冲突。据11月14日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每日报告数据:本轮冲突已造成以方1200余人、巴方1.1万余人死亡,另有百余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罹难。
巴以冲突热度超过陷入僵持状态的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月4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称:“巴以冲突把人们的注意力自俄乌冲突上转移,希望西方盟友增加对乌的军事援助。”冯德莱恩则表示:“欧盟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金融援助。”
早在10月20日,拜登政府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总额为106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及以色列的特别拨款法案。但国会众议院在11月2日只单独批准了其中对以的143亿美元拨款,且拜登扬言要否决该法案。
次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24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而这已是其对乌拨款额度里所剩不多的选项。虽然拜登称“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同等重要”,但西方近期对乌军事援助速度有放缓迹象。
一个隐藏的问题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产能,是否已无法支持两线军援?如今,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军工产能吃紧的背后,一个个巨兽还将陆续张开血盆大口。
战争背后的吞金怪兽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滋养,美国的军事工业得以空前飞跃。1949年,美国及西欧诸国成立了共同制定战略计划,统一指挥及训练;装备标准化生产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织内的军工实体得以截长补短,深度整合。
1955年,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冷战格局正式确立。两大组织的兵工厂为了假想中的未来大规模战争马力全开,产能拉满。
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发表离任前的告别演说,其中提到:“我们不能让军事工业复合体成为我国政策的决定者,否则我们将会失去自由和独立”—军工复合体首次为世人熟知。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规劝显然收效甚微,到1970年,美国军费达到834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了44%;到1977年,更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24年预算则达到8860亿美元。在某些战争决策中,军工复合体疑似成为幕后推手。
冷战持续期间,美苏相继在越南与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在这两场耗时多年的局部战争中,两国虽未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常规武器消耗量极大,军费节节攀升,愈发蚕食GDP,阿富汗战争更成为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
冷战后期,军事承包商转换了设计思路,一些富有科幻感、设计意图为对敌军进行科技碾压打击的高科技武器项目纷纷出现。如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F-117攻击机,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B-2轰炸机,美国联合防务公司研制的“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