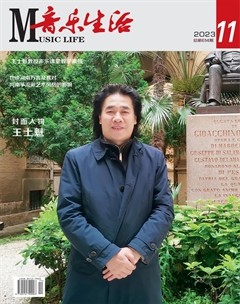“妙”这个古典叙词的意旨,实在是一个处境非常奇特、别致的艺术审美范畴。对于中国人的日常感悟、喟叹来说,人们在讲它的时候其实心里就已对话语表述对象给到了一个神奇的定位空间了——妙,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这同时也就赋予了这个谈论对象及话题思维的性质将趋向于某种神秘的、虚空的或清灵的情境之中。然而,什么是“妙”?怎样才算是“妙”?“妙”往何处寻?仔细思量一下,如何能够及时又合理地回答好这些问题,现实的难度显然是存在的。
国人的文化殊性和族性传统使然,自古以来在很多方面的直觉意识,就是世代相传、直接去实施体用,而非西方学理化的那种前置论证,因此,中国人会自然地沿袭、承继对特定范畴相关义涵的理解,也就决定了像“妙”这样的概念意识实际上处于全然渗透于国人生存方式中的状态,以一种非刻意诠释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语言表述世界和思维指向当中。因而,笔者对这一审美叙词及其范畴内涵进行相关艺术哲学与音乐批评式的论道,是想要试图厘清一些“妙”与艺术、与音乐之间的那些值得人去思考与表述的趣味所在。
一、“妙”在艺术广义性上的可感知处
笔者认为,“妙”审美范畴在艺术广义性的可感知处,往往会和“绝”这样的主体审美印象相互勾连。“妙”的表述和范畴辐射区域,在国人千年以来的形色各样的艺术实践活动中,有着非常普泛和浸润性的表达样式。作为音乐人,在艺术广义、普适的理解角度来审查所能接触到的众多相关“妙”之表象性的感触点,不仅是笔者后续要就“妙”的殊性角度作出进一步考量认知的基本前提,也是音乐工作者可以此触类旁通、形成相关题材创作可能性的艺术同理之处。对此,笔者将从诗歌与文学、书法与雕塑、形体与舞蹈等艺术论域中,选择自我阈限范围内可感知的较为经典、较为鲜明之处,来进行挂一漏万的阐发。
中国经典诗歌、文学佳作中有很多着意于“妙”审美范畴的艺术化描绘,这就把“妙”的超凡的情趣性,引领到读者们心灵所神往的去处了。如: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尤其是相关到“太虚幻境”,相关到戏中戏般的古诗词意境阐发[1],相关到特定人物性格、内心戏剧性变化等处的具体化和细腻描写,就是尤为神妙与出彩的;如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2]的那种愁思之妙,南唐后主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3]的缠绵之妙,李清照“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4]的情窦初开之妙,辛弃疾“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5]的疏冷之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6]的幡然悟道的境界之妙,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眼》[7]中那种虚写恋人瞳孔美如海洋、实描肺腑缠绵爱意的魔幻之妙等……,也都是诗歌文字美感诠释方式中的点睛之笔、神来之语。
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充斥着对“妙”审美范畴的体用艺道,这已在世界书写艺术形态中形成了其构型气质独树一帜、意蕴风格与流派形态璀璨万化的情势。喜爱和迷恋书法艺术的国人,上至帝王将相(如曹操创意地省去笔画且有雄浑之妙的魏书、宋徽宗在清瘦字架间兼有丰润飘逸之妙态的瘦金体、历代皇族达士们所题墨宝等),下至专攻书法写作艺术的各方名家(如王羲之、赵孟頫等人的行书、草书等)以及体现了“高手在民间”情境的工匠手笔(如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家庭中仍保留、继承的毛笔字书写习惯,如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及遗存现象较强的潮汕、福建、江南地区仍存在普遍的书写高手,如在遍及大江南北的大批底层手工业制作者中属于行家里手的涂绘手画等),都是各自在书法艺术审美共性中所幻化出来的、不一而足的主体个性表达。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管窥”书法妙道的一个精微之处,那就是书写者运笔刹那间的“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的笔锋妙势——这是一种懂得“进退往复”的巧妙变化运作,是充满了哲思审美趣味来对“妙”做以孕化之道的经典体现。
而人们如果时常留意到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古代宗教艺术中那些比比皆是的表达形式,就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雕刻及雕塑艺术当中,尤其是对那些特定体态、举止和神态等塑型的神韵上,就卓越地体现着中国人對“妙”审美范畴在艺术彰显状态上的把控能力和审美质感。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多年前在一次偶然的田园风情游历中,曾有幸见过一处偏僻乡间的艺术水平极佳的窗棂木雕,所刻画题材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凤鸟”纹饰。非常有趣但也极为遗憾的是,原本应是完全对称立美的两扇窗棂,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在世面貌和“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的主体审美体验——其中一扇窗棂的雕刻显然是古人原作的遗存,而另一扇窗棂原图由于年代久远而朽坏被后人重新复刻,这恰好为人们无声地诠释出了艺术创造力上的审美差距。两者间有某种高下立判、云壤之别的感受,因为古人原作中的凤鸟雕形,其翔飞感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圆熟且妙韵十足的;而现代复刻的那一面,只是生硬相似了鸟儿外形,却毫无古人手作艺术形象中的那种难以言传的灵动生气。
笔者记忆印象比较深刻的主体趣谈言论之一,是著名的符号学理论家苏珊·朗格曾经用令人耳目一新的“虚幻”观念,来具体形容过其学理研讨范围中的各种艺术形态给人的审美感受,特别是说到了舞蹈艺术在其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虚幻的力”的观点,朗格的这个审美诠释在笔者看来,是十分新奇又非常贴切、巧妙地指出了舞蹈艺术的某种本质化的审美特征。借由这个认识基础,笔者也同理地认为,舞蹈的非凡妙态,正是在于舞者们能够凭借了人之曼妙的、带有神奇想象力的肢体语言,来很好地在艺术性的灵魂层面进行着种种美好的艺术设计与审美表达。国人特别喜爱的众多的中国舞中的舞蹈审美元素,也是在着力凸显着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的柔美、舒展、写意等审美情愫。而能够集约地体现出这种中国舞蹈审美方式的地方,应到中国古典审美情致极浓、极高的戏曲舞蹈当中,去找寻美的踪迹与感受性,因为戏曲舞蹈的表演,会以更加丰富和系统化的、充满了审美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种种妙趣,它们又融汇于同样精致又震撼的戏曲脸谱、戏曲服饰和戏曲舞台有关人体写意性形态的众多表演程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