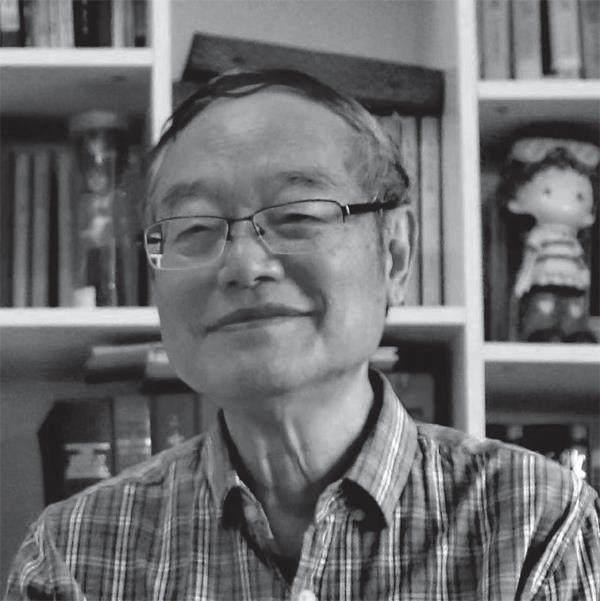
在对于物质媒介感觉终止的地方,诗才真正开始。诗是心灵的艺术,它摆脱一切物质媒介的束缚,获得深远的情思空间。由于心灵化程度很高,所以诗是云中之光,水中之味,花中之香,女中之态,唯能会心,难以言传。诗是一种无言的沉默。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陶渊明《饮酒之五》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视刀环歌》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周易》说“言不尽意”,都是切中要害之论。
一经说破,语言就会破坏诗,赶走诗。在诗歌写作上,诗人是“肉眼闭而心眼开”;在诗歌表达上,诗人是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
由于在以瞬间顿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非逻辑性的表达方式和非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上的亲密,在悟境上的相同寻求,诗与禅靠得很近。在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的轨迹几乎同步。陆游的《赠王伯长主簿》说:“学诗大略似参禅,目下功夫二十年。”明僧普荷说:“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但是,顿悟之后,禅一般“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得不记录的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的传灯录和语录,称为公案)。诗却必须托诸文字。诗不能言,但它又是文学,它必须言,所谓“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言无言,就是诗歌艺术的永恒难题;以不沉默传达沉默,就是诗人展示才华的机会。语言,成了诗歌艺术创作的最大障碍;征服语言,驾驭语言,又是诗人的最大成功。
本来,诗对于古代中国就十分重要。闻一多是这样阐述的:“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文学的历史动向》)诗的语言更为重要。“以诗取仕”,主要就是测试诗歌语言水平。在《论语》中,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懂诗歌,一个人连语言能力都没有。
那么,诗的语言是什么呢?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持有这种看法的古人实在不少。金人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卷36中写道:“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尔,有所记叙之谓文,吟咏情性之为诗,其为言语则一也。”新诗的最早“尝试”者胡适对此心中也没有底。白话诗的“白话”是什么,胡适说不清楚。所以,当年的守旧派说他太俗,革新派又说他太文。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里写道:“诗之文字原不异于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于文之文法。”元好问还在叙事与抒情上区别诗与散文,胡适则更彻底,干脆将诗与散文的界碑全部打碎了。他还更明确地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其二,诗使用的是一种与散文语言不搭界的另类语言,散文使用的语言绝对不能入诗,否则就是诗的降格和破坏。正是由于这种见解,所以在中外诗歌史上出现过许多“官司”。莎士比亚在他的诗剧里的一些用词遭到指责。20世纪30年代,在重庆,有过“飞机”一词能否入诗的争论,有人建议以“铁鸟”一词代之。在俄罗斯,未来派诗人1912年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里曾宣布“有痛恨存在于他们之前的语言的权利”,“有任意制造词和制造新字以增加词汇总量的权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诗歌并没有承认这种“权利”。
其三,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存在层次上的区别。唐人刘禹锡说:“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明人苏伯衡说:“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清诗话》收录了吴乔的《答万季埜诗问》,共有27篇精彩的答问,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尔。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美,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一为饭,一为酒,提升程度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不同。比之于饭,酒当然更精致,更精美,更精华,更精神。
在西方,有“用左手写散文,用右手写诗”之说,也与中国古人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