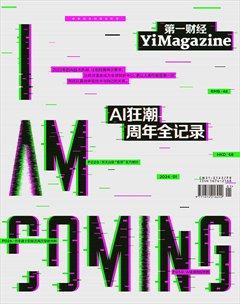记得有一次回南方老家,从金华站出来,昏暗的出口处传来“咝咝”的声音,好似入了高能蛇阵。走得近了,方知是揽客。拉客人嘴里齐齐吐出“兰溪、兰溪”,这些重音后置的“溪”汇聚在一起,被地下通道的气流放大,俨然蛇群吐芯。如果换成女声,一定更蛊惑人。
之所以揽客,是因为兰溪与高铁尚无缘分,中转带来了商机。挨着兰溪方向,金华府过去有个老北门就叫兰溪门。这兰溪门的命名,似乎也是对兰溪码头来客的一种招揽。1636年,旅行家徐霞客从老家江阴南下,在兰溪码头乘船来到金华,就在兰溪门外一家旅店住下。
可如果回看历史,虽然大部分时间为金华府所辖,近代之前的金华,其繁华程度,却是比不上三江汇流、六省通衢的兰溪的。也有人形容义乌与金华近30年的关系,是兰溪版本的延续。在1933年浙赣铁路筑成之前,兰溪是福建、江西等地与京沪平津等地联通的水路上仅次于杭州的最大商埠。正所谓,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
河道
我一直在追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50年前在中国考察的路线。在1871年一次浙皖苏之行的日记里,他记录下一个面临海运威胁的兰溪:“从广州到杭州的交通要道过去虽然曾令此地(兰溪)十分繁荣,但现在却因为有了沿海的蒸汽船运而黯然失色了。从广州运往北方的货物不再选择经由浅滩众多的内河运输,而是从海上用汽轮运往上海,要不了几天的时间就到了。”
李希霍芬还留意到从屯溪过新安江到沪杭的水路开始超过兰江上游下行的贸易,“兰溪这里的河运远比在严州府(建德)附近开始的新安江重要得多,但现在新安江上的茶叶运输比前者的运输总量还多。”
都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但对于一直以内网水路为命脉的兰溪来说,海运的开启,特别是铁路网的密集铺设,给兰溪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浙赣铁路开通当年,作家郁达夫受铁路局之邀乘坐游览,撰写游记,认真推广这条新线路。诗人被兰溪优美的风景触动,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兰溪栖真寺题壁诗》和《过兰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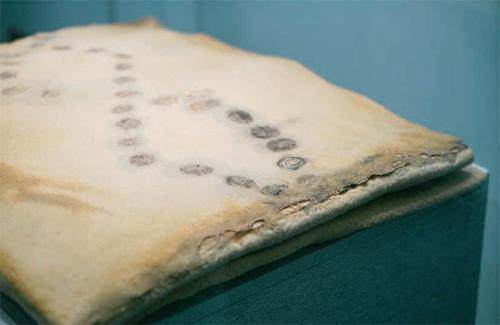


在兰溪博物馆的“芥子园书画展”展厅,另一位兰溪人、摄影艺术家郎静山拍摄的兰溪山水黑白银盐照片,以山水画的装裱方式呈现。和郁达夫一样,郎静山也在那次受邀乘坐浙赣线的名人旅行团之列。
兰溪人曹聚仁是民国著名报人,他在一篇怀念另一个兰溪人—李渔的文章里借机怀念故乡过去的繁华:如果时光倒转四五十年前,海内外知道有金华这样的城市。那时的金华,还只是乡村少女,兰溪早已是“摩登狗儿”,跟上海那么“摩登”,“小小兰溪比苏州”,非虚语也。
历数兰江舟楫南来北往的历史,总觉得自北入南多是客,从南往北货居多。
1670年,自徐霞客过兰溪后又过了三十多年,兰溪人李渔受福建总督之邀从南京走水路入闽,也正是因为路过家门,他借机在乔王二姬和家班成员的簇拥下回金华和兰溪省亲,真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一百多年后的178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奉命来华为康熙皇帝祝寿,从热河返国时他被允许走内河穿越中国。
使团成员对清帝国的山川景观和典章制度都充满了好奇,因此留下了详实的航行记录。据当时的随行大臣斯当东记载,使团人员在兰溪稍作休整,补充日用品。在进入衢江前,由大船换乘小船。斯当东很注意换船这个细节,对小船做了细致的描述:约十二呎(即英尺,约合3.66米)宽,七十呎(约合21.34米)长,船头和船尾俱是尖形;船底是平的,吃水很浅;帆是布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