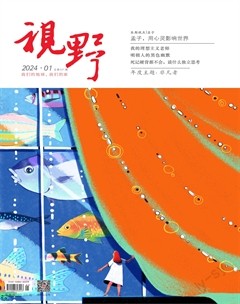何謂大丈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之术,用今天的术语简单讲就是国家外交策略,它虽体现为游走在国君们之间的诸多纵横家个人的辩难与谋略,但背后承载的是一个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因此纵横术首先体现的就不再是一种基于个人的道德哲学,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它很接近现代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谓“政治首先就是区分友敌”的思想。合纵,就是联合一些同样弱小的国家作为朋友,而以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敌人,从而求得对敌人的暂时均势,是以守为攻;连横,就是选择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朋友,而以其他相对弱小国家作为敌人,从而求得对敌人的暂时优势,是以攻为守。
在一个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时空里,对单个国家而言,纵横术本身作为一种国家自我保全的政治哲学,有其相当的价值。在孔子本人,也并非完全弃绝纵横之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齐国欲伐鲁,鲁国危亡之际,孔子召集弟子,问谁能救父母之邦,并默许最善辩论的子贡去游说诸国,结果呢,“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所持秘诀,无非就是抓住各个国君的心理要害,以利诱之,使之互相攻战,环环相扣,借力打力,从而让本来离战争最近的鲁国反倒安然无恙,这不正是纵横之术吗?孔子能够知道子贡在这方面的长处,可见圣人也并非不擅纵横术,只是对圣人而言,纵横术只是不得已而用之,故而子贡虽立奇功,也只是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孔子亦不会夸他。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景春的错误所在了。他不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纵横术,而是将之视作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手段,并用“大丈夫”这个极具个人色彩的词汇来称赞那些名扬一时的纵横家,就难免要遭到孟子的批驳了。
孟子的批驳,是从词源学的角度入手,他不和景春纠缠在公孙衍、张仪是否为大丈夫的意见判断上,而是先厘清“大丈夫”的基本概念。你明白什么叫大丈夫吗?这一问非常重要,是由意见转向知识的一问。
我们今天所谓的丈夫,仅仅相对于妻子而言,是生理层面配偶的代称,而在古时,丈夫是指行过冠礼的男子,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指代。“丈夫之冠,父命之”,命之的具体内容,孟子很奇怪地省略了,而在“女子之嫁,母命之”的后面,却进一步说得很详细。那么问题就来了,孟子为什么要省略“父命之”的内容呢?
从出自汉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对冠礼的父命略窥一二,“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仪礼·士冠礼》),“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仪礼》还是《礼记》,对丈夫之冠,都强调一个“顺”字。虽然这个“顺”,是对君上而言,与孟子在下文中斥为妾妇之道的“顺”并不一样,但毕竟字面相通,而在一场简短的对话中,倘若再这么细微地区分概念,实在是有点累赘,也许正因为如此,孟子干脆将父命的内容当作景春完全应该知道的常识,加以舍弃,集中笔力来阐发他对妾妇之道的理解,以此达到暗讽纵横家的目的。
或者,孟子的用心一直都不在“丈夫”,而在“大丈夫”。他之所以省略了对丈夫冠礼中父命的陈述,可能正是为其随后对“大丈夫”的一段精彩阐发,打开话语空间。“大”这个字,甲骨文里就是一个立着的人的象形,他有头有手有脚,挺立于天地之间。天大,地大,故人亦大。汉儒讲礼,但礼规范出的是一个社会人,是丈夫。而反复诵读最后一段流荡千年而不衰的铿锵言辞,我们领略到的,与其说是符合社会共同体规范的丈夫形象,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独立之人格、超越具体社会和统治体、能真正堪与天地并称三才的理想的人,是之为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