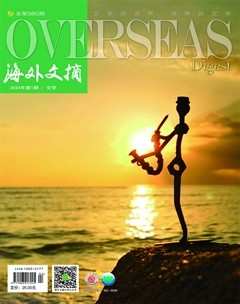事情还要从唐元和十年(815)说起。
在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一事上,白居易忠耿直言,越位先于谏官言事。同时,受到道德上有所谓“浮华无行”“甚伤名教”瑕疵的攻击后,从官官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较好的职位上,被贬为江州司马。谏言本是他的职责所在,道德瑕疵纯属污蔑,但是,贬他没商量。
白居易来到江州,转眼就是一年。
元和十一年(816)秋天,在风景如画的庐山,白居易在郡守的陪同下,亲自到北麓香炉峰下选址,设计并营建一座草堂。第二年春天,草堂落成后,邀请了河南的元集虚、范阳的张允中、南阳人张深之、东西二林寺的长老等二十二位好朋友,摆上斋饭茶果,吟诗品茗,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
此后,白居易在草堂隐居近三年,撰有《庐山草堂记》。文中详细描述周围的美妙风景和居住在草堂里的心理享受。“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覶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都城长安没有这等美妙美景。在山水之间建一座草堂,读书写诗,安放身心,精神闲适愉快。“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许由洗耳,淡泊名利。醉酒狂歌,颇有陶渊明风采。
居住在这里,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住上一天,精神舒畅安宁;住上两天,身心恬美通泰;住上三天,感觉妙不可言。郡守很关照我,庐山以灵胜美景抚慰我心。如此天地人和,夫复何求?夜深灯亮,白居易兴奋地写信给元稹,分享此地的美妙风景。“封题之时,不觉欲曙。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或坐或睡。又闻山猿谷鸟,哀鸣啾啾。”夜不能寐,信中一直聊到东方欲晓。
境有心造,心随境换。草堂窗外的风景,确实让人沉迷忘我。草堂内的家具陈设,更是让人清心寡欲。白居易的草堂装饰,走的是“极简”路线。堂中,设四个木榻,两扇素屏,一张漆琴。另有儒、道、佛书各三两卷。当然,还有古琴一张。建房所用的木材,仅用斧子砍削成型,不再用油漆彩绘。墙壁涂上泥巴即可,不再用石灰粉刷白。砌台阶所用的石头是捡来的,窗户用白纸糊成,帘子用竹子所编,帐幕用麻布织就。这些简洁又环保。
书房,最能体现文人的个性和审美趣味。白居易草堂里的书房,同样是“极简”风。只有一根朱藤杖,帮他远行,登山游玩。一张蟠木几,方便他坐卧其上,憩息冥想。两扇素屏风,掩屏隔离睡觉。元和十三年(818)的一天,夜深人静,月光如水,白居易独自一人抚琴。“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琴声如诉,饱含来自天际的幽情,只有他自己能听得懂。
这三件极简风格的家具,确是白居易的最爱。他为每件家具赋诗一首,组成《三谣》,极富文人情怀。仔细品读,其实这也是白居易内心世界的自我关照,也是他内心思想情绪的真实表达和寄托。
其中,《蟠木谣》是这样唱的: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无用于人。
下拥肿而上辚菌,桷不桷兮轮不轮。
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栋;诸侯斫大辂兮,材又不中。
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尔为几,承吾臂支吾颐而已矣。
不伤尔性,不枉尔理。尔怏怏为几之外,无所用尔。
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裴回?
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
如同现在的手串,几案是古代文人的标配。《庄子·齐物论》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那时没有现在的椅子凳子,坐在“隐机”上玄思长歌,这是当时很时尚的做派。文人的几案,以用珍稀的木材和华贵装饰为美。白居易只有“不中乎器,无用于人”的蟠木几。他把这样的材质比喻成自己,身段放得低到尘土之中。白居易从心理上已经接受这一事实,江州司马不过是一个“不器”的“病夫”罢了。
白居易在蟠木几上侧身而卧,他对着围在身边的两扇素屏风自言自语,内心独白,吟成一首《素屏谣》: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
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
边鸾之花鸟,张垛之松石?
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
欲尔保真而全白。
他对着素屏风一连串的自问,表白自己从不流俗于喧哗与骚动。素屏风为白居易建构出无欲无求的精神世界。“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人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素屏谣》)清风明月本无价,陪伴草堂里的自己。白云透过窗户来来往往,环绕在我的床边,我在心中涵养着浩然之气。与那些表面的光鲜相比,《孟子》说的“浩然之气”,更能体现一个文人的价值。
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
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
贵豪待此方悦目,晏然寝卧乎其中。
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
爾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素屏谣》)
豪门大族家里的屏风装饰豪华,这是社会普遍潮流。白居易不愿赶时髦,草堂内的屏风和蟠木几一样“不材”,他只追求器物本真的素雅。它们只有放置在草堂中,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与主人成为平等的朋友。这一切,很有《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味道。
此时,四十四岁的白居易正值壮年,却用朱藤做了一柄手杖。平时把玩欣赏,出门策杖远游。他还专门写了首《朱藤谣》:
朱藤朱藤,温如红玉,直如朱绳。
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
唯此朱藤,实随我来。
……
吾独一身,赖尔为二。
或水或陆,自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
吾本两足,得尔为三。
紫霄峰头,黄石岩下。松门石磴,不通舆马。
吾与尔披云拔水,环山绕野。
二年蹋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