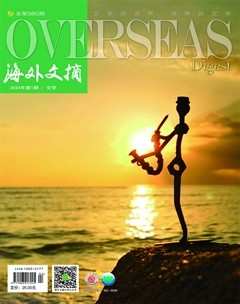那服解药的方子是东晋陶渊明开出的,主要药材是酒菊花、豆苗什么的,药引子是酒。药方就写在庐山脚下的田园之上。
北宋的苏轼,依照这个药方,又添加了几味药材,药方就写在从扬州、惠州到儋州的贬谪路上,并亲自烧火煎熬几十年,把它炮制成治愈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
仔细分析,陶渊明的药方并非无中生有。他总结、综合了庄子的逍遥思想,又兼收并蓄了西晋和东晋如“竹林七贤”等士人把奇山异水、林泉景致作为审美对象,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风尚,扬弃他们放纵享乐,对自己、家庭和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装疯卖傻式荒诞做派,保留下来爱酒的嗜好,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提炼出这剂药方——“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陶渊明《九日闲居》)
当然,陶渊明提炼药方的过程也是心灵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精神修炼。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在义熙元年(405)四十一岁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当地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尊敬。他一气之下,从只干了八十多天的彭城县令岗位上愤然辞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只是他理想中的洒脱状态。“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也是幻想中的闲适生活。
陶渊明是否故作潇洒之态,今人不得而知,但对于出身于世族之家、有条件“富裕”和“贤达”的陶渊明来说,这种选择是难得的,也是超前的。
鲁迅曾说过:“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证明着他并非整天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鲁迅的文章似匕首、刀枪,总能一针见血。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出身高贵,少年时意气风发,有鲲鹏万里之志,但对现实社会、个人仕途失望之后,收敛巨翅,“鸟倦飞而知还”,把身心安放在田野山林之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看似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其实,回到山野自然之中很容易,但吃穿住行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全家人生存需要必要的技术能力,但他缺乏。“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生命需要吃喝拉撒睡,才能活下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生存就要劳动,劳动是辛苦的。“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陶渊明自觉从士人转换成农民身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与村民四邻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由此,头戴草帽、被太阳晒得皮肤黑红的陶渊明,已把自己混同于庄稼汉,从外貌和思想上已与其他文人区别开来。
这确实是一个精神蜕变的过程。
从古至今,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开始时都是儒家孔孟之徒,思想上总把“仕”与“耕”、当官与劳动相对立。陶渊明主动选择“耕”,确实很“另类”。他在“贫富常交战”的现实矛盾和心灵冲突中,亲自体验着种田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感受着田野里的诗意和生命存在的自然之道。“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劳动给他带来快乐,但他又不混同于一般的农夫。“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一个“聊”字,心迹暴露。陶渊明在思想上一直都有士大夫的自觉,始终以东晋王朝的旧臣自重。比如,他对权臣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不满。即使全家在生活揭不开锅的时候,对刘裕手下的大将、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的酒肉粮食,也予以拒绝,孤傲清高的性情,不曾改变。
远离尘世,走进山水田园,仅仅是很多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消遣意趣。只有一位陶渊明,通过亲自耕作劳动的生活实践,从把山水田园作为单一审美对象的精神享受,拓展为与田野劳动相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人生思考,从而为文人士大夫找到另一条归向自然、安放身心的道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他真正从精神和心灵上,享受到“复得返自然”的妙处。
以今之视昔,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求长生不老(形),不求流芳千古(影),只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之中,躬耕田野,看透生死,养真守拙,远离红尘。“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该来的,总会到来,那就来了再说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既然人一出生,就走在死亡的路上,那就与草木共荣枯,与山川同安眠。陶渊明任性自然,心有所归,身有所依,神有所寄,不喜不惧,在饮酒中达到超脱、本真的生命境界,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心灵澄明广阔。他丰富的精神和生命境界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及后世的士人群体,一直影响到今天。
陶渊明的生命之河像一泓清泉,浇灌和抚慰着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心田。但是,后人大都追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却不愿践行陶渊明农事耕作的艰辛。
南梁朝的太子萧统是位文艺青年,最早重视陶渊明,著有《陶渊明传》。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对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命钦佩不已。如此精神价值取向,注定他这位太子的悲凉命运。但幸运的是,他从历史长河的沙粒中,为后人打捞出《古诗十九首》,亲自编选并留下《昭明文选》,这些文字存世,远比他登上皇位更有历史意义,流芳也会更加久远。
到了唐代,“诗圣”杜甫一生维艰,曾说过“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但他一生心里总放不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身在草堂,心向庙堂,对陶渊明只是嘴上碎碎念而已。白居易等人也曾对陶渊明青睐过短暂时刻。“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郊陶潜体诗十六首》)他被贬江州司马时,距离陶渊明篱笆墙下的黄菊花并不太远。“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韦应物为洛阳丞时,也曾有“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采菊露未唏,举头见秋山”的清高姿态,但终不能适应土地上的牛粪味道。唐代另一位诗人储光曦同样如此,“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壶”,他们的着眼点是诗酒风雅,而不是真的到田野里去“种豆南山下”“晨興理荒秽”。仕途一旦出现转机,得到皇上重用,很快就忘记陶潜是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