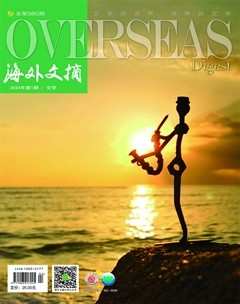出生于北宋时代的王十朋(1112—1171),自号“梅溪”,是一位典型的奔跑在浙江乐清县梅溪村田野里的乡村少年。
在两宋文人士大夫群星荟萃的时代,王十朋从出身、名气、诗文和政业绩等几个侧面来看,他与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曾巩、黄庭坚、司马光、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等众人相比,绝对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坚守和气节,完成了一位乡村少年的两次人生逆袭,不得不为他点赞。至今,有关他的爱情故事仍活跃在江南地区的戏剧舞台上,表达着社会普通老百姓心中固有的价值判断。
作为乡村少年,王十朋的第一次人生逆袭很艰难,但确实是蛮“拼”的。王十朋与两宋诸多“明星”文人出身官宦世家、人脉资源广泛不同,他出生在农户之家,往前数八辈子都没有家人做仕宦的记录,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少年。或许是基因突变的缘故,他少年早慧,颖悟强记,七岁入私塾,十四岁学通经史,诗文名闻遐迩。他少年时忧国忧民的志向和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从十七岁开始,他正式从师攻读经学诗文,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二十九岁那年,初试失利。其后,他边聚徒讲学,半工半读,苦读备考,历经十五年的屡败屡战,终于大器晚成。
绍兴二十七年(1157),他已经四十六岁。宋高宗主持殿试,亲擢王十朋为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鸣惊人天下知。别人怀宝剑,他有笔如刀,成为宋孝宗和宋光宗两位皇帝的老师。入朝为官后,他一直力主抗金恢复中原的政治主张,与宋高宗为主的议和派尿不到一个壶里,被排斥回乡。宋孝宗即位后,王十朋仍不改主张,但与宋孝宗的抗金思路合上了拍。后来,王十朋在泉州做市长时,德能勤绩廉各方面都甚佳,群众评价很高。乾道五年(1169)冬天,当王十朋卸任离开泉州时,人民群众自发站立在街道两旁,依依不舍,涕泪横飞,苦苦挽留。有些人甚至采取极端做法,把他必经之路上的桥梁拆断,逼他留下,他不得不绕道“逃”走。后来,当地百姓重新修复桥梁,名为“梅溪桥”。
宋代的科举制度,使贫寒庶族可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王十朋就是这一制度的获益者。“我岂不欲仕,时命不吾与。”读书改变命运,参加科考十五年,在四十六岁高中状元,为时不晚。作为一位乡村少年,要说应该珍惜这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可王十朋不这么想。他明确表示自己读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科考,而是为求道。“读书不知道,言语徒自工。求道匪云远,近在义命中。吾儒有仲尼,道德无比崇……孰识孝与弟,理与神明通。为臣不知此,事上焉能忠。”(《畋亩十首·其三》)明理孝悌,为臣尽忠。加强自身人格修养的完善,向孔子致敬,才是读书之正道。“我家素孤寒,金玉苦无储……性情乃良田,学问为耘锄。”(《和韩符读书城南示孟甲孟乙》)家里贫穷如洗,但读书是为了更好地修身养性,并为自己身后留下清白的名声,不能让后人非议自己。“兀兀窗下士,笔耕志良苦。黄卷对圣贤,慷慨深自许……贪荣无百年,贻谤有千古。丈夫宜自贵,清议重刀斧。”(《畋亩十首·其八》)以圣賢为师,淡泊名利,千万不能让自己遗臭万年。这就是王十朋同学的“论读书与自我修养”。
“君子之学,求于为己而已,初无心于求用也。学既足乎已用,自藏于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无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资,遇其当可用之时,著其能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归之于天,而有所不顾恤焉。”每个人为了自己开始读书,而后是为了致用。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就要不负韶华,大干一场。但当自己不被重用时,皆是天意,不要有任何怨言,一定要修炼好自己的心性,乐天认命,必有福报。“君子之道有三。其未达也,修其所为;用其既达也,行其所当用;不幸而不遇,则处其所不用。修其所为,用则能尽已;行其所当用,则能尽人;处其所不用,则能尽天。”(《君子能为可用论》)作为一位读书人,王十朋明白自己为什么而读书,努力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君子,尤其是当读书人不受重用、人生失意的时候,更需要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不用之用”,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方,不怨不伤,乐天知命,其精神境界确实高于一般读书做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