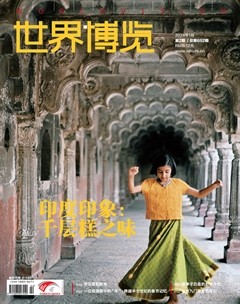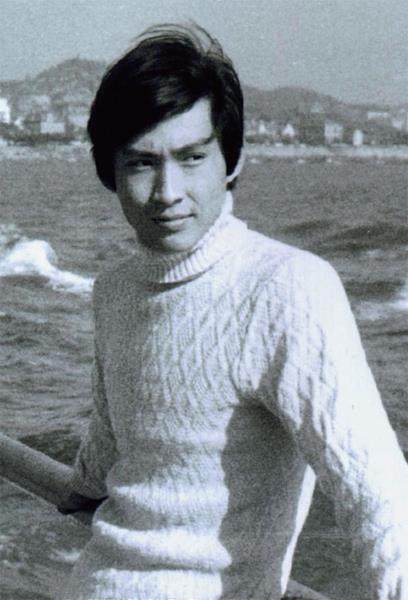
我曾经和朋友说:好日子过得快!记得那年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第一场放映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后,一位韩国导演过来和我说,看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拍出这样的电影?我心想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龄怎么就开始怀旧了。我是过春节前的一月生人,现在我家兄弟姐妹唯一留下的一张老照片,是我一岁时的合影,大家穿着新年的衣服,表情释然,只有我皱着眉头,不知是冬日的寒冷,还是一岁的我已经开始怀旧了。岁月如梭,转眼真是到了怀旧的年纪,而伴随我们成长的春节,让人念念不忘。

童年记忆
我有记忆的时候,是在幼儿园整托,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这样的日子对孩子而言是委屈的,度日如年。五岁那年,快上小学了,父亲从幼儿园接走我,领着我走在雪后的南河沿,我们默默走着,只听见脚下踩雪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幼小的我内心窃喜,终于可以不去幼儿园了,终于可以和家人每天在一起了。那时院里的小朋友常聚到我家,母亲因此从王府井买回一台收音机,大家每天围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广播,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
我们成长在生活条件匮乏的时代,也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一切都理所当然,也没关心过成年人的艰辛,我记得那时候高大的榆树被扒下树皮,露出白色的树干,百姓艰难地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小学到中学,在进入大学前,日子过得基本差不多,每年就盼着年早点来,可以放假,吃好吃的,仿佛人生的忙碌就为这一天。
小学有几年,我们也不上课,父母根本顾不上孩子,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游荡在附近的皇家园林,今天去故宫,明天去景山,天天变换地方,爬上爬下,衣服破了也顾不上。一天傍晚,父亲对下班的母亲说,怎么还不给孩子准备过年的衣服,大概到了年根儿,父亲在提醒母亲,我愣愣地望着他们,才意识到这是有些埋怨母亲,因为不管日子如何不易,每当我们出门,母亲总会给我们打扮得有模有样。
长大一些时,开始对美有些感觉,每到过年,总要穿身新衣服,那时有一身卡其布藏蓝色中山装就很高兴,再穿一双白色塑料底黑色条绒面儿棉鞋就很风光了。记得小时候,母亲闲适在家,就会给我们纳鞋底儿,为每个孩子取纸样儿,用不同的布料,做出不同的鞋子,特别是过年,总要让我们每人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让我们感到既欢乐又温馨,觉得过年真好。
年味儿
大年三十儿,是国人最在意的日子,这一天,母亲就会忙碌起来,上午打扫房间,玻璃窗擦得光亮透明,窗前挂上手工钩织的窗帘,透过镂空图案,红色的窗花若隐若现,屋里收拾得洁净而祥和。下午开始炸丸子,先炸素丸子,再炸肉丸子,然后做上一盆肉皮冻,同时炸几条带鱼,最后炖上一锅红烧肉。想起当年在怀柔插队,因为知青不太会干农活儿,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在火车站装卸货物,那天中午我在車站小饭馆买了一碗红烧肉,放在饭盒里,我把瘦肉咬下解馋,肥肉就连汤一起泼掉了。一位村里的中年妇女此刻见状,随口说,你怎么给扔掉了呀,你给我呀!我说,那是剩的,我咬过的。她接着说,那怕什么呀!瞬间我有些自责,可想想我吃剩下的是不应该给别人吃的。那时人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别说吃红烧肉,就是吃肉都非常奢侈。我也是偶然为之,只有过春节才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正经的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