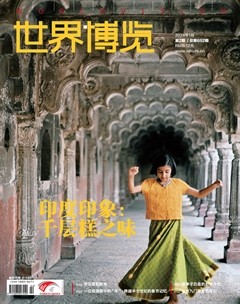在马伯庸的小说《两京十五日》里,为保皇位,以朱瞻基為首的主角团一路沿大运河北上,日夜兼程杀回北京,却被拦在紫禁城外。工程大牛、技术宅、安南太监“木呆子”阮安闪亮登场,正是在这位北京皇城营造者的指引之下,主角们才由暗道直入宫闱,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历险。故事余记里,马伯庸特意花了些笔墨,摘录了几条语涉阮安的史料记载。故纸堆里的只言片语,搭建起关于这位传奇太监的点滴记忆,映出他为紫禁城规划蓝图、为北京九门修缮角楼、为燕北乡里疏浚河道的劳碌身影。
在阮安的记忆里,故乡安南是炎热而动荡的远方。少年时代,耳边听闻无休无止的不安消息:权臣弑君了,大明遣使问罪了,大明使节被追杀了,明朝大兵压境了……来不及逃亡的时候,明军已经兵临城下。万军簇拥的主将,是靖难之役功臣张玉之子张辅。遥想当初,张玉是明成祖朱棣起兵之际的左膀右臂,夺取燕京九门立下首功,东昌之战中,在千军万马里舍身救主。对于功臣兼救命恩人的儿子,朱棣委以重任,临行前嘱咐张辅,马到功成后记得选拔一些能工巧匠和青年才俊,朝廷正缺人才。
南征顺风顺水,明军势如破竹,将安南重新纳入版图。张辅不敢怠慢圣谕,精心挑选一万多人,供皇帝在宫中差遣。按照惯例,张辅下令将他们净身。阮安名列其中,这时他真正见识了亡国之耻:纵使逃过一死,却落得净身入宫的境地,未览世间繁华,再不是少年郎。更冤的是,待到朱棣在南京见到长途跋涉而来的一万多安南太监,止不住埋怨张辅:让你阉了抗命刁民以示皇威,怎么把这么多无罪少年也阉了?或许心怀愧疚,朱棣对这批安南太监恩遇有加,专门赏赐御寒衣物,允许他们读书识字,这无疑打破了明太祖旧制。在朱元璋的教诲里,太监不得识字,不识字就难以干政,宫闱之内就少了许多潜在危险。
蛰伏宫中
朱棣也有自己的苦衷,靖难之役虽说赢了,天下归心却只是假象。文臣武将,都对他的得位不正颇有微词,夷灭方孝孺十族,也挡不住士大夫的腹诽。新政初立,没有心腹可用,自然只能仰仗身边之人。这批安南太监年轻聪慧,在朝野没有半点根基,更不会党同伐异。日理万机的朱棣,甚至专门抽出时间,考核安南太监的文化水平。阮安头脑灵活,却不善言辞。在殿前真正令皇帝眼前一亮的人,是与之一同入宫的范弘。这位小太监伶牙俐齿,又颇懂些中原掌故,让朱棣龙颜大悦,特意安排他研习经史、磨炼文笔,留在东宫侍奉太子。
未得恩宠,阮安倒不太在意,没有东宫近水楼台的殊遇,他也乐得逃离钩心斗角和蝇营狗苟。只因他发现了另一方天地,足以寄情其中。皇宫的殿台楼阁,让阮安心驰神往,他不仅喜爱那些建筑的恢宏与精巧,更沉迷于背后的构思与技艺,整日钻研工程营造,沉浸在草图与数字的世界。完成日常劳作之后,阮安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窗子,他隐约能听见同乡太监们窃窃私语,交换着内闱八卦:皇帝今天异常焦躁,哪个妃子添置新玩意,哪个宫女多嘴多舌遭罚。但在狭小的房间,阮安却在琢磨着全然不同的一档子事儿:宫殿如何内圆外方、皇城怎样排水防涝、门楼能否兼容工事。熟知宫中的规矩和八卦,是晋升的必由之途,工程营造却似乎是屠龙之术,空有一身本领,却找不到地方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