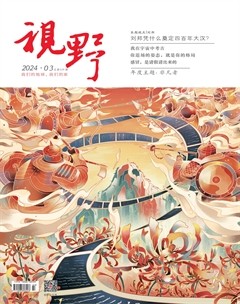一
在节奏如驰的医院,一舟是个不入群的女孩。单薄的她,穿着同样单薄的T恤和牛仔裤,绑一根麻花辫,发丝被㿠白的日光灯氲出毛茸茸的边沿。她安静地坐在血液内科候诊区最后排的角落里,蜷着腿,手里捧一本卡通记事本,不说话。
那天,我带着一份紧急会诊邀请,从另一个院区的病房赶来,请血液内科的医生协助评估病情。我看到一舟的胳膊,臂弯处凿满针眼。我瞥见她有些苍白的脸和嘴唇。她十六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白血病——好发于少年儿童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门诊医生调取了一舟的病历。意外的是,并没有白血病的征兆。血常规的结果也只有一处异常: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绝对值减低。“是恶性疾病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像。”
我们继续查阅了一舟的其他检查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在短短半年里,她竟然先后做过二十余种检查,且有些项目做过不止一次。
一舟的手指在发抖,嘴角微微抽搐。她的母亲站在旁边,几次欲言又止。确认其他的检查都没有异常,我刚要解释,一舟忽然哭了。
“我要做穿刺,”她抽噎着说,“我一定是白血病,请您给我开检查。”
“没有证据指向白血病,”接诊医生皱起眉头,“大概率是感染。”
“我必须做穿刺,”一舟拼命地摇头,“给我开检查,我不怕痛。”
“听医生的话。”她的母亲说。
一舟缩在凳子上,浑身颤栗。她张开嘴,开始大口呼吸,好像喘不过气似的。
我把一舟的母亲喊出诊室。关上门的刹那,她也哭了,略显佝偻的脊背靠在门框,双手捂住脸颊。我认真地打量着她——面前是个约莫四十岁的女人,矮胖,绾发,发胶在灯下折出不协调的高光,穿一件发皱起球且不合节令的大衣,手背上青筋遍布,白色的纹路嵌进皮肤,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爬满瘢痕,关节弯曲,像一台老旧的水车,随着动作隐约呻吟。
片刻,她做了个冗长的深呼吸,手掌捋过额头和鬓发。几缕垂落的发丝被发胶短暂地固着,须臾又垂下来,在她皲裂的唇边,随着鼻息轻轻地晃。
“孩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问。
“哪里都不舒服。”她苦笑着说。
“具体是什么表现?”我继续追问。
“有时肚子疼,有时腿没力气。”她说,“还有心慌。”
顿了一顿,她接着说:“她上网查过很多专业资料,懂得不少。”
“病毒感染也会导致这个指标减低,但过几天就会恢复。”我继续解释道,“最近换季变温,学校人流量大,容易发生感冒流行。”
她揉了揉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
半晌,她再次深呼吸,鼓足勇气,嗓音喑哑。
“去年秋天,孩子就休学了。”
二
我用工作微信添加了一舟的母亲为好友。
她的头像是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昵称叫作“山川”。
我再次看见一舟的时候,是在精神科病房。那段时间,病房里住着很多年轻的患者。工娱室里,常有十几岁的孩子在剪纸、画画。间或,也会骑动感单车、打乒乓球。护士站旁的墙壁上悬着一块正方形红漆木板,上面拓印着金色的倒“福”。木板旁边,挂着一串千纸鹤形状的琉璃风铃。每每有孩子出院,经过护士站时,总要摇晃一下。
叮铃——
他们说,这是胜利的号角。
一舟仍然不入群。我接管病床的时候,她独自蜷坐在床上,披散着长发,怀抱那本卡通记事本,安静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
那幅水彩画,是上一个住在48床的病患画的。她十七岁,已经在抑郁中挣扎五年。水彩画中,是一簇勾勒精致的雏菊,七八朵,白瓣黄蕊,各自矜敛地张扬。花枝下面是赭色的泥土,荆棘丛生,笔触粗糙遒劲。她在出院的前一天画了这幅画。随后,这幅画被装裱起来,挂在48床对面的墙上。
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故而更宽敞些。一张病床、一张陪护床、一座床头柜、一台沙发、一方袖珍的小木桌。窗户向南,总是整洁明净。上了锁,只能打开一条巴掌宽的窄缝。米色窗帘上,细腻的针脚绣着鸢尾和黄莺。
也许还在生气,一舟并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很无奈。那天我向她母亲建议去精神科就诊的时候,她先是惊愕,旋即恼怒道:“你竟然说孩子是精神病?”
一舟的入院初诊是焦慮症。她的母亲还是与前日相同的装束,只是没打发胶,发丝愈显猖獗。陪护期间,她常站在工娱室外,或者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