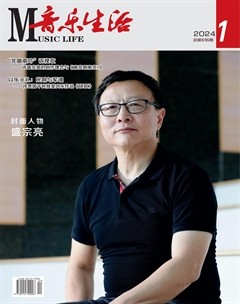作曲家贾国平创作的民族室内乐作品《铙歌》2019年11月7日受邀于国家大剧院,在“风华正茂”中国当代作品专场音乐会中进行首演。作为当晚的压轴作品,《铙歌》无愧于这一殊荣,卓实至名归。不论于笔者还是当场的乐迷而言,都是一种情与思的交流,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2021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特以此部作品向中国军人致敬,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2023年,笔者于立春时节又有幸听赏《铙歌》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演出实况录像,由乐不经再次而发澎湃敬畏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自秦风汉月的辉煌历史,至隋唐盛世的气象万千。西北苍茫大地孕育、承载的千年昌盛,都离不开这片厚土塬上人们的胸襟开阔、粗犷豪迈与自强不息。《铙歌》不单单是一部作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文化的弘扬。这场跨越千年的“军乐”演绎,深度诠释了民族精神与国乐气概。
此部作品《铙歌》的创作较于贾国平教授所写的室内乐作品风格一改从前,从中华文化的写意者化身为民族气魄的响育人。并无刻意进行序列数控的预设与十二音的创作手法,抛开“数理”的創作方式,着眼于速与力的设计,从而达到民族乐器在听觉感官上的震撼感。不妨可说,这部作品作曲家在以史于明意、欲念以抒情。“每一部新作品的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蜕变的过程,每一首新作品我都试图寻求与自古至今的他者以及与自我以往作品的不同。期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每一部新作能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1]这是贾教授对自我每部新作的准则与期欲,力求不拘泥于既定模式,从而不固守于自我,实现突破。《铙歌》是作曲家首次用全为中国乐器的乐队编制“编码”而成的民族室内乐。为何此部作品令人心生澎湃之情?下面跟着笔者一同踏寻这部作品背后引人入胜的“解码”之旅。
一、史
《铙歌》这部作品是“先锋”对于“传统”的延续。是作曲家理性与感性碰撞下的产物,不难发现,这部作品有别于其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品。不是往常诗意的传达,亦不是传统文化的普通传承,是在用民族声音抒发民族情、赞颂民族志。
“铙歌”并未被简单地理解为“歌辞”,而是被视为一种有着深厚内涵的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与内涵的“史诗”。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铙歌”这一音乐形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的传承。它表达了较为隐约的历史观,叙述的是较为完整的被“知识化”的历史。一些诗歌以铙歌命名用来叙战功歌功颂德,如南朝何承天《朱路篇》:“三军且莫喧,听我奏铙歌。”、赵翼《从军征缅甸》诗:“传语健儿休笑我,凯旋时节要铙歌。”贾国平教授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军乐,类似于军队仪式的音乐。
“铙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种类,属于诗歌的范畴,它与音乐紧密相连,是一种语言艺术。然既可以通过歌唱的方式表达,也可以通过吟诵的方式展示。其内容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可以涵盖各种主题和情感。在古代,有一种名为采诗的制度,通过收集和整理诗歌,来观察风土民俗,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和需求,从而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大汉王朝正式设立了乐府机构。乐府机构积极收集了各地的民谣,这些民谣反映了汉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人民情感与文化风貌,将它们精心收藏,备于在各种重要场合中使用。其目的在于表达对天地的敬畏、祭祀祖先的尊重、朝廷庄重的赞拜、诸侯间的团结会盟、对胜利的祝贺以及表达宴飨宾客的热烈氛围。[2]“铙歌”体裁通晓的是历史的脉搏与时代的赞歌,然文化特质主要通过“以乐示礼”的礼乐精神体现出来。
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沉淀与积累,“铙歌”已然蜕变为一种独特的体裁,一种承载着人文底蕴的“音乐符号”。它巧妙地构筑起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紧密相连的音乐语言符号。《铙歌》这部作品产生的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能指的乐谱符号、音响符号与作为所指的思想情感、心灵状态与纪实事件之间,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浑然天成的意指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天地之间的鸿蒙气息,汇聚成一幅美妙绝伦的音乐画卷。在这画卷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历史的辉煌与变迁,感受到了人文精神的厚重与深邃。这使得《铙歌》成为一部超越时空的杰作,融合了古今中外的音乐智慧,成为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正是这种富有人文属性的音乐符号,使得《铙歌》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
在《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贾国平教授说到:他依据山西梆子戏素材创作的民族室内乐新作《铙歌》,这部作品的音乐材料植根于他的故乡山西,“铙歌”的概念取自于汉乐府鼓吹乐,并以此表达对于冼星海音乐精神的致敬。[3]除此之外,此部作品亦有另一种乐用,其中的“意”请详见后文。作曲家通过乐谱与音响符号赋予特定的思想情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从读者角度出发,音响的听觉上,直观的感受到外柔内刚的即时感与浓厚的戏曲元素。在音乐内部,作曲家沿袭了“铙歌”的徵调式与五声调式的传统定弦。通过半音游移的对置,模拟戏曲的腔调。表达了作曲家中国传统音乐与乐礼和而一体写意的美学观念。
《铙歌》作品器乐的编制中,打击乐是重中之重,几近贯穿始终。极强的音响张力展现了贾国平教授对于故乡山西地域的风格特征的把控以及对于“鼓吹乐”的诠释。“鼓吹”即是军乐,来自于秦汉时期山西西北部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鼓吹”的形成与北狄、西域音乐有重要关联;以游牧为生的边地北狄人,常在马上演奏乐笳、角、铙、鼓、排箫等乐器[4],是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结合的音乐。故此,这部作品另一巧思在于配器:笛子是领奏声部,打击乐则担任着氛围的烘托与气势的营造。
拨开表层面纱,作品本身所孕育的人文属性与历史内涵极为丰富。“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5]鼓吹乐自汉代起具有重要的政治属性与功能。《铙歌》作品所指其一塑造出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英勇形象;其二反映着美与真实相映成趣、艺术与生活相互融合的美学观念;其三流露着国家的信仰与民族的担当。
二、形
《铙歌》作为一种军队的仪式音乐,古代军中乐歌——马上乐。贾国平教授设定“军乐”格调时,着重关注了速度与力度的设计,展现出音乐中的速度与激情。贾国平教授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陕西秦腔与山西晋剧的板腔形态。通过采用“垛板”的形态,以每分钟300拍的飞速节奏,充分展现了军乐作品所具有的迅疾、紧凑、刚毅有力的特点。整部作品音乐结构清晰分明,紧凑独特,旋律简洁明快,展现出极高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譬如,在乐曲Ⅰ部分,他巧妙地运用了五连音的节奏形式,贯穿全篇。整齐匀称的步伐节奏好似蓄势待发。如同骑兵铮铮有力的马蹄声,又似部队军礼时整齐划一的步伐,寓意着“声声铿锵”的坚定决心,彰显着信仰与力量的融合。
《铙歌》体裁的转引与音乐素材借取看似巧妙的结合,实则暗含着的是千年文化的承载、是无畏的敬意、是由心而发的赞颂。所以在《铙歌》这部作品中,作曲家选择用邦笛和曲笛作为领奏乐器,以民族打击乐贯穿全曲,作为整部乐曲气韵的基调。冼星海曾说道:中国民间的打击乐是独立的。有着独特的民族韵味,是中国音化的体现,亦是军乐中核心的乐器成员。全曲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用罗马数字Ⅰ、Ⅱ、Ⅲ、Ⅳ来表示。依据开始的“角色”设定,贾国平教授对乐曲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异显精妙,各个乐器在不同的声部中起到了互相依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