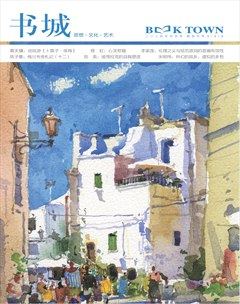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是法兰西学院首位女院士。让·德·奥姆松(Jean d’Ormesson)在学院接纳尤瑟纳尔的典礼上称赞她书写生命的深度:“一个小说家是用不着为之立传的,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传记。”而尤瑟纳尔的“自传”小说并非囿于个人与现实,而是以历史为经,异域为纬,呈现为一种集体性传述。正是与历史的深度融合,将她导向超越历史的维度,使“无所不在的永恒”回荡于她作品构筑的世界上空。这种或可称之“去伦理化”的写作,不再作为单纯的历史叙事,更是表达生命形式与情感的永恒记忆。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小说集《东方故事集》(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集中反映了尤瑟纳尔的异域文化情怀。这个集子的东方叙事不限于地理意义的“东方”,亦取材于东欧巴尔干等地,其中远东题材的故事只有《王浮得救记》(下文称《王浮》)和《源氏公子最后的爱情》(下文称《源氏》)两篇。这两篇故事都具有浓厚、离奇的神话色彩。作者在本书后记中交代,她的东方书写试图“突出……某些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个观点由书中《失去头颅的迦梨》那篇主人公的独白集中表达出来—“我纯洁的头被安放到卑贱之躯上了……我既有所欲,又有所不欲;我痛苦,却又享乐;我嫌恶生,却又惧怕死。”尤瑟纳尔借印度女神之口,言说的却是西方形而上学中典型的人:渴望超越时间归附永恒,却又不得不在时间的洪流中挣扎。
然而,尤瑟纳尔不会满足于直接描述某种人的形象,创造史诗或一般文学隐含的道德模范。在《王浮》和《源氏》中,她将人置于更广阔的图景下,在其中,人总是与永恒有紧密联系,这种永恒之物在两篇小说中体现为一条隐线—我称之为“形象神话”,这里“形象”一词来自《王浮》那篇。画家王浮喜爱的是“事物的形象,而不是事物本身”,以最纯粹的态度揣摩一切形象,以至于欣赏“死者面容上这种青色”和“弟子的鲜血在碧玉地面上留下的美丽的绯红色痕迹”。为了本然地体验形象,王浮须尽可能地摆脱观看事物时的流俗认识对他的干扰。因此,在创作女人肖像时,“没有一个女人不真实到可以充当他的模特,凌却可以做到,因为他不是女人”—王浮并不在意常识意义上的俊男美女,只在意纯感受性的形象与现实的距离。对他而言,“形象”剥离了事物的日常意义,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退回认识之初婴孩般的知觉,这种纯粹丰富的知觉赋予了形象审美的魔力。这便是神话的起源。它塑造出一种隐秘而静肃的审美氛围,独立于个体存在的喧嚣。
在尤瑟纳尔这两篇远东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为神话所形塑和控制,或是在永恒的召唤中沉默和谛听。由此看来,仅以东方主义或异国情调的概念看待这些小说,或是单独分析其中主要人物,都不足以阐释其独特魅力。为理解这种神奇的叙事手法,本文着眼于形象神话如何渗透在各种人物关系之中,进而解析尤氏之悲—喜剧与可怖的寓言。
迷狂:环绕人间神的信徒
周游于两个世界之间,王浮逐渐领悟出从人间走向形象世界的海图,其最后的画作彻底打破形象与现实的界限,用柔软的笔触在世界的坚冷处晕开了一层墨色的裂口,艺术通过它得以影响现实,救赎生命。逃生不再是奇迹,而是一个深沉型艺术家必然的归宿。我们可以说,王浮是自足的游世者,只事创作,并于周游与创作中续写、变换整个形象神话的故事。
然而小说中仅此一位从容的俳人,更多的则是在神话里“信徒—人间神”这个对子两端相互凝视的人。汉皇与源氏就是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人间神:他们并非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善牧,代表着“将人类灵魂带回到一种前青春期的纯真状态”和声色之欲与灵魂之欲的分裂,反而像印度牧歌中兼具神圣性、神秘性的肉体,不是理念的神,而是可被知觉的神:“不仅能够唤起爱,而且回应爱。”而信徒,则通过欲望人间神而欲望永恒。
《王浮》中的汉皇是偏执的,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汉皇周身作为信徒的众臣捧月式的肃穆所塑造。在控诉王浮欺君时,他曾谈起自己的童年,“我被故意放到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成长。为了不让我的纯真受到人心的玷污,我根本无法接触到那些躁动不安的我未来的臣民们”。“人心”本是常人皆有的,而汉皇在臣子眼中只是不近常人的至美形象的肉身。众臣筑起高墙,以此隔离人间最真实的生死—“一道高墙将花园与外部世界隔开,以免从死狗和战场的尸首上掠过的风吹来袭扰皇帝的衣袖”,汉皇作为常人的身份于是被遗忘在伊甸园,这里没有情欲、时间与战争,只剩下形象的纯美、神话的承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