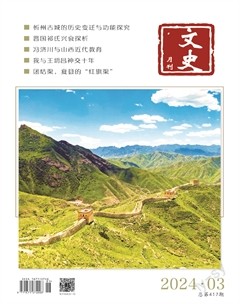先从一副对联说起。
小时候听父亲说,早年间我们洪洞县(原赵城县)马牧村里许家四老爷有文才。四老爷怎样有文才,父亲没说,我也没听别人说起过。白纸黑字的许氏家乘更难见到。那个年代,能往脑子里装的净是新东西。
四十年前我参加工作,教研组里有一位李荫堂老师,“右派”刚平反,跟我和小建很谈得来。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临汾师范,“右派”帽子没有压垮他的才艺,吹拉弹唱,随时就能来上一段。性情也诙谐,喜欢掌故。有天突然对我说:你们马牧许家四老爷,是个秀才,写过副有名的对子。马牧在赵城县是个大村镇,寺庙多,唱戏酬神比别的村子就多,“马牧发大财,一年唱八台”么。请的都是好戏班,戏散了,人还不散,看四邻八村的秀才们在台口比赛刷对子。场面挺热闹,每回压轴的都是许家四老爷。有一年是小蛋的戏《白蛇传》,小蛋演白娘子,四老爷拟了一副嵌名对:
小蛮腰跪于大佛殿前不让春风杨柳;
蛋青衫穿在白蛇身上俨然秋水芙蓉。
李老师扶了扶眼镜,接着说:小蛮腰对蛋青衫,春风杨柳对秋水芙蓉,你看对得多好!
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了,我开始喜欢一些旧东西,对这段掌故印象很深。
多年后才知道,小蛋大名李有福,是晋南有名的戏班福盛班的台柱子。蒲剧名旦王存才也在这个戏班,后来名气盖过小蛋,民间流传“误了收秋打夏,不误存才的《挂画》”。许家四老爷的嵌名联传神写照,也算给百姓喜爱的蒲剧名角留下一点口碑资料。
当时忘了问李老师,这段掌故听谁讲的,他父亲么?他的父亲也是秀才,大概跟四老爷一起看过戏,也在台口刷过对子吧。他家在高公,离马牧七八里路。
李老师去世好几年了。小建的怀念文章说到有几次李老师忽然绷起黑脸,佯装发脾气,冲着我俩说:“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们俩,都离我远远的,都到县里和省里去算了!”也许他会掐算吧,不几年小建调进县城,业余写作,出版几本诗集、长篇小说,当上县作协主席。我后来也到了省城。看过小建的文章,我俩微信语音通话,聊起四十年前在万安中学的那段时光,自然也说到上面的掌故——已经是掌故的掌故了。
许家四老爷是谁?
三年前父亲重病住院直到去世,我回老家住了些日子。有位远亲拿来一册新印的《马牧许氏家谱》,他是许氏十五世后裔,在村里开饭馆,主营“许家酥肉”。看过家谱中的碑版文字和相关资料,我才粗知许氏家族的兴衰,以及四老爷许寯(字穉芸)的一鳞半爪。
马牧许氏是清代晋商旺族,嘉庆、道光年间经营盐业发达起来,富甲赵城。道光《赵城县志》载有许氏八世、九世舍粥施衣、出膏火帮贫寒子弟读书的善行义举。大约到十世,许氏家业进入鼎盛期,在赵城、洪洞、平阳、霍州、山东等地开着商号;水地八百亩,村东一字儿排开四盘水磨,在汾河东岸的后河头村也有几盘水磨。村中五十多个院落,鳞次栉比:风驰楼、看家楼、粮店、当铺、赁铺、醋坊、染坊、药房、油坊院、糟坊院、祠堂、家庙、花园……整个一座规模宏大的许家庄园。
我念高中时,每天都要经过油坊院、看家楼断垣,再拐进旗杆院巷,经过半亩园遗址、旗杆院。庄园整体上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但从幸存下来的一所宅院、一处拐角、一面影壁、一对门环、一个柱础、一幅砖雕……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富贵荣华。
到十一世,许氏家族进入文脉鼎盛期。许墨林、许荐廷两个亲兄弟,加上堂兄许成章,同治六年(1867年)同榜中举,时人誉为“一门之内,人文鹊起”。十年后,墨林妹夫、石止村的崔瀛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过三十年,墨林三子许喆在山西大学堂毕业,宣统皇帝“赏给进士出身”,许家有了旗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