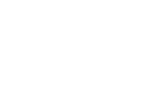她們的父亲死了,人们替做妹妹的松了一口气。老人瘫痪在床十四年,妹妹一个人全勤照顾了五千一百多天,给父亲喂了一万五千多次饭,换了三万多次便盆,擦了一万多次身体,洗了一万多次澡,说了几万句鼓励与安慰的话,以她的孝顺、温柔维护了父亲病中的尊严,以及活下去的健康心态。
老人是在深夜突然离世的。这一晚,妹妹蔷薇像往常一样,拧开父亲房间的台灯,打算给父亲翻身,更换尿不湿。她推动父亲身体时才感觉到不对。怔了半晌,复轻轻摇晃父亲,就像小时候向父亲索要什么东西时所做的那样,那时父亲总会满足她。这次,她要父亲醒来,但父亲没能让她如愿。
蔷薇撒手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异味,一点也不像病人生活的地方,是她用双手将这里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给父亲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床头柜上的全家福照片虽旧却清晰,两个小女孩站在父母身前:姐姐穿着白色蕾丝边超短裙,蓬松的长发随意散落,脸上晴空万里——一个美人胚;妹妹一身校服,短发齐耳。她们的牙齿雪白发亮。
蔷薇是在姐姐的阴影下成长的。姐姐鲜亮聪明,衬托得她暗淡笨拙。姐姐大她三岁,却从小有一股让她慑服的力量。姐姐读书时总拿第一,蔷薇也有点崇拜姐姐。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姐姐就把家务活推到蔷薇身上,她只需坐在那儿,拉出讲恐怖故事的架势,就能让蔷薇乖乖地洗碗、拖地。姐姐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更是成为家族的宠儿。后来离家求学,在外结婚生子,渐渐成了家中遥远的贵客。每次回来谈笑风生,逗得父母开怀大笑,从来不进厨房,双手也没有触碰过油污、垃圾。姐姐也不是刻意表现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和成功人士的养尊处优,她从小就是这种做派,是与生俱来的。
有一瞬间,蔷薇很想给姐姐打电话,她想在电话里大哭一场,告诉姐姐,父亲走了,她们两姐妹已是父母双亡的人了。世界塌下来了。她需要姐姐撑起一个角,让她透透气。她第二次拿起电话,拨了两个数字,最终还是放弃了,并且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理智告诉她,凌晨两点钟的电话是毫无意义的,只会破坏姐姐的好梦,更何况眼下并没有需要姐姐帮忙处理的事情。省城这么远,姐姐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何必大半夜地搅乱姐姐一家子,等到早晨再打电话也不迟。
外面是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滂沱大雨。山洪险情严峻,蔷薇的儿子正在一线办公,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儿媳妇和两个小孙子住在河对岸。大雨冲淡了父亲的死亡。人们都在祈祷大雨停歇。
蔷薇开始默默给父亲梳头、洗脸,最后一次为父亲擦身,为他换上了他最喜欢的套装,那是母亲生前给他买的生日礼物。蔷薇的短发渐渐凌乱,遮着半边脸,弯腰劳动的背影显得单薄而又虔诚。她还不知道悲伤,像往常照顾父亲那样,处理着现场的狼藉,平静地给殡仪馆打电话,条理清晰,一一安排好相关事务。
打点好这些,天还没亮,雨势依旧凶猛。房间里没有了父亲的呼吸声,忽然间变得空空荡荡。空气里有一丝冰凉。她擦拭着全家福。父亲戴着眼镜,他脾性温和。短发的母亲端庄大方,她曾经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也是单位里的一把手,可惜已在五年前离世。蔷薇原本有机会和一个不错的男人发展关系,那一年儿子考上重点中学,她成为部门领导,但是母亲突然中风,她同时要照顾两个生病的老人,忙得连与他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母亲住院三个月,姐姐来医院看过两回,每次都像领导视察,匆匆小聚,连夜驱车赶回省城,对每晚睡行军床陪伴母亲的蔷薇没有表现出一点愧疚。母亲出院后坐了几年轮椅,直到去世。姐姐从没真正照顾过母亲,她很少回来,推轮椅陪母亲散步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姐姐始终忙着运用她的知识与高智商打着她的投资经营大算盘,敞开钱袋子迎接大笔大笔的金钱滚落进来。她那双白皙的、手背满是“富贵窝”的手,是一件创造财富的完美工具。
蔷薇陪着父亲,想了些与父亲有关的事,而这些记忆又都与姐姐相关。姐姐远远地生活着,依旧深深影响着这个家庭。就像童年那样,蔷薇照样崇拜姐姐,对姐姐的宽容,超过了她们的母亲。她已年近六十,退休已经提上日程,上了年纪后有斑出现在皮肤上,她对此并不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