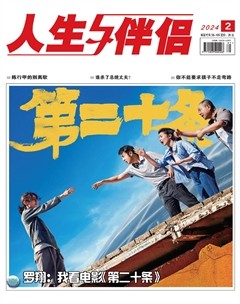在中学读书时,扎昔娜姆每次搭车回家的路上都能碰到游客,他们会问她是不是摩梭人,接下来的问题几乎都是一致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知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
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的泸沽湖畔,生活着一支特殊的族群,他们是摩梭人,人口约2万左右。因为恋人之间“夜合晨离”“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文化,以及母系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互联网上走红,又被称为“女儿国”和“母系氏族活化石”。
近些年,“走婚”作为摩梭文化中的重要一项,已不复过去的盛况,外出者日渐增多,选择“走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時代的巨轮之下,摩梭人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现代文明。
摩梭人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时代浪潮下,他们又将怎样应对不可逆的现代化?
一
生活在几十人的大家庭中,年幼时的扎昔娜姆“分不清哪个才是自己的亲妈”。这一现象不是孤例,不少摩梭小孩都曾有过类似体验。
摩梭语里,妈妈的姐妹一律叫“阿妈”,大姨二姨之间只有“大妈妈”和“小妈妈”的区别。加上长辈对待孩子们不存在私心,分辨生母就变得更为困难。
“每个小孩都会享受很多来自大人的爱,比如我大姨有好吃的,她不会先给自己的孩子,而是给每个孩子平分。”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云南乡下,过着一种“基本上吃不上肉”的贫瘠生活,扎昔娜姆依旧在爱河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上小学时,扎昔娜姆每天放学后的任务是到地里割猪草,她通常约着几个小伙伴一起,“边玩边干活”。到了周末,家长交给他们的任务会加重,要找到比平时多两三倍的猪草回家,扎昔娜姆最得意的也是这个时候,她会和伙伴趁机跳进泸沽湖里游泳、嬉戏。
有一种叫波叶海菜花(又名“水性杨花”)的植物,就长在湖里,猪很喜欢吃它的叶子。扎昔娜姆便在游泳时,潜到水下收集绿叶。“我们就是边游泳边玩,顺便把这个活儿给干了”,她说。
湖边也牵连着汝亨多吉的美好回忆。
现年48岁的汝亨多吉是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颇乐意提及过去的生活。他对泸沽湖的初印象,是“美丽”和“纯净”。汝亨多吉记得,泸沽湖边的自然沙滩上长有高大的树木,他和小伙伴就经常躲在树底下玩闹,老人则凑在一起聊闲天。
他还喜欢和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疯跑,山间、田野,都是孩子们天然的游乐场。
相比扎昔娜姆,汝亨多吉幼时的生活则更加贫苦。家中物资匮乏,很多物品需要共用,汝亨多吉和兄弟姐妹们总是来回穿那仅有的几件衣服。内裤,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穿过,当时的乡村人压根“没有那个概念”。
汝亨多吉小时候贪玩,屁股处的布料磨破了,妈妈就再找一块布,一针一线帮他缝上。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家里是特别温暖的”“精神很富足”。
他也时常怀念奶奶。小时候家里养的鸡下了蛋,奶奶会捡回家煮给汝亨多吉吃。老人的兜里还经常装着苹果干、梨干等小零嘴,见了面就拿给他。
这些画面像是刻在汝亨多吉脑子里,一听到相应的关键词,回忆就自动涌现。
在摩梭大家庭中,不仅有家屋文化,还有家姓,那“不是男人的姓,不是女人的姓,是大家共有的姓”。
嫁娶也不存在,双方依旧生活在原本的家庭中,没有利益的纠葛,不必在意家庭情况、彩礼,也无须长辈的认可,“是充分的自由恋爱”。
有一句话说,“爱情是自己的,亲情是大家的。”走婚是自己的事情,喜欢什么样的人,谁也不会来管。
汝亨多吉留恋早年时候的自由自在,身处偏僻宁静的地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寨之间的人们重礼仪、讲礼节,每个人身上都流露出淳朴、友善的一面。
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二
不知从哪一刻起,那种自然生态中的美和孩提时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泸沽湖也不复往日模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湖边的大树被砍伐,木房子改建成水泥房,自然沙滩也修筑成栈道,放眼望去,四周尽是工业的痕迹,汝亨多吉始终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反差”。
很多时候,行走在熟悉的地方,看着街道上日益生长出新的名字,汝亨多吉反倒觉得,自己才是个异乡人。他感到孤独,面对曾经生养自己的土地,有一种陌生感,“整个环境,完全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