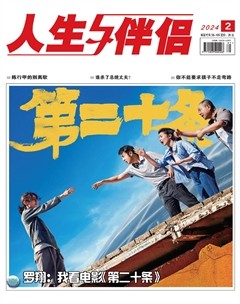30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我和弟弟终于不情不愿地离开“春晚”,从明亮温暖的房子里踏入漆黑阴冷的夜幕中,去给素未谋面的姥姥、姥爷、爷爷,以及几无印象的奶奶烧纸。我心里带着对母亲的怨气,以及错过精彩节目的遗憾,默默跟在母亲身后。当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走过西门时,蓦得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有一天,不是妈妈带我们去烧纸,而是我们去给妈妈烧纸……我不由打个激灵,紧跑两步追上步履匆忙的母亲,挽起她的胳膊。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母亲过世了,我意志消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那压抑的心情十分逼真,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有一天我打算走出房间,于是去照镜子,想对自己笑一下,没想到镜子里的自己却在哭。醒来后,枕头湿了一大片,我哭着跑到父母房间,发现母亲笑意盈盈地坐在床上,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终生难忘。
又过了若干年,老公的姥姥过世,我们去奔丧。跪在一群孝子贤孙中间,我想着终有一日我的母亲也会离开,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谁承想,我的母亲竟在一年后,真的撒手人寰。
当梦境变为现实,才知道现实比梦境残酷太多。从未目睹至亲离世的我彻底垮了,无边的黑暗、凄凉、无助,像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我既绝望又神经质,时而躺在床上悔恨交加,时而像打了鸡血一样查阅资料,“到底哪里做错了”“有没有时空隧道”“死后有灵魂吗”“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一年后,因闭门不出而内分泌失调、身材严重走样的我终于活着走出家门。在与“死亡”的漫长对峙中,我“败下阵来”,接受了“人固有一死”的千古真理。自此,我不再安慰有丧亲之痛的人,只是告诉他(她)“时间会抚平一切”。
这段惨绝人寰的经历也让我深刻体悟到中国的死亡教育多么匮乏。生与死是人生最大的两个命题,“除生死无大事,出鸿宇尽微尘”,但由于国人对“死亡”的忌讳,使得死亡教育一直缺席,很多人都是在至亲死亡或自己死亡的过程中才首次接触死亡,那种恐惧与茫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