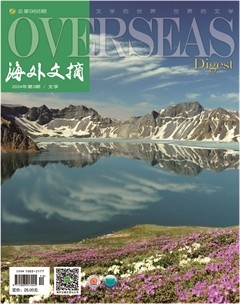我从警第二年,抓了一个毒贩。男的。
那一年,我点子其实挺背。
一次执行完任务,我卸下弹夹,但忘了还有一颗子弹上了膛,一扣扳机,啪,子弹冲窗而出,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洞,裂纹向四周可怕地伸展。我吓傻了,满脸涨红,火辣火烧。坐我对面的余姐惊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腿下洇出殷殷血迹。
她流产了。
我有深深的罪孽感,郁郁不能忘,这比随后遭受的处分还致命。
女朋友又以走火为由,和我分了手。我走火,她走路,从微信朋友圈看她很快乐,我就知道所有的“弹痕”只留在了我身上。
简直祸不单行,我深陷痛苦之中,来不知所以来,去不知所以去,潦倒地过了几个月。好在,有牛队的开导和照顾,才不至于成了废人。靠着牛队父亲牛法科是我初中班主任,我们就亲密得像兄弟。当然,他是兄,我是弟。有时候,他是凶,我是蒂。枯萎的花蒂。
立功的机会终究还是到了。通过一个线人,我在辖区成功地抓到了一个毒贩。我是单独行动的。我想,结局无非两种,我干掉他,或者他干掉我,当然,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男毒贩显然很菜,没跟我们打过交道,甚至哪怕只是在内心里都没跟我们过过招儿,几个回合就招了同伙——他的妻子。
逮捕他妻子那天,我在市场外一棵树后蹲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但还把最后一丝温暖投向这个山抱水绕的县城,建筑物的阴影砸在地面,梧桐叶伸出金黄的手掌与风相迎。秋蝉声声,鸟鸣不止。要不是恰巧在那些天,我会被这一幅秋景美哭。
女人刚从市场出来,我就从身后蹿过去把她铐起来。
你干啥?你干啥?抓流氓呀。她尖叫起来,显然以为遇到了劫色。等反应过来,才一边反抗,一边说,警察,我咋子了,买棒子骨也犯法嗦?她的手里死死抓着塑料袋,两根骨头还在空中晃荡,散出猪肉才有的那种肥腻气味。
少废话。我凶巴巴地打断她,那些天,遇到谁我都没有好声气。
啷个歪干啥?我要给女儿熬汤。她虚虚地朝我看一眼,而后就带点儿要辨识我是谁的意思。这让我觉得,我的脸像张二维码,她要“嘀”的一声扫一扫。
到公安局去熬。到了公安局有你熬的,熬棒子骨那种,我保证。我铐着她,穿过马路。这在外人看来,我像扯着一个大只动物。我没用任何遮挡物,手铐亮闪闪的,在夕阳下多了一层黄晕的光。从菜市场出来的人聚集了一大堆,商店的店员也站到门前。作为一天的收尾,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也算没辜负那一天。我想,总会有人要为这一天做上标记,多年后还能从众多的时日中挑拣出来,奔涌到舌尖下,作为吓唬幼儿不要哭闹的药引。
女人脸一下红了,不再吵闹,默默地被我拽着往前。那一刻,我忘记了几个月来累积的情绪,并被一种激越所激荡,夕阳成了我的加冕礼,众人的瞩目也是。从警以来,我一直都是配角,是谨慎的观察者。
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
快到公安局门口,女人突然停下来,童彤,你是童彤,对不对?我认识你。
驚诧地回过头,我脸上写满了疑惑。
我确信,我们并不认识。
见我大写着不解,女人说,你不认识我了嗦?我们是同学。
同学?我再次上下打量她。棕色头发,盘起来,用水晶发卡一绾,精致、简约。白皙的左耳,戴着枚小耳钉。她眼里有了惊喜的光,盖住了刚才的恐惧,那样子像是赴约同学见面会,只是地点恰巧在公安局门口。实事求是地说,那张脸没有毒贩的萎靡和凌乱,而是让人有无话找话也要把天聊下去的动力。只是很遗憾,我没在那张脸上找到任何一点有关“同学”的信息,也许是时光之土一层一层地掩埋了它们。
我是黄菊英,坐你前面,初中那哈儿,啷个出名的,呵呵!黄菊英自嘲地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我恍然,像一颗种子努力拱开一层层掩埋的泥土,带着要在阳光中伸开两片幼芽的那种渴望。得承认,她变了,确实变了,变得好看了,变得精致了,变得高挑了,变得完全认不出了。但仔细分辨,细长眼没变,额头上一条疤痕还在,尤其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和一颗龅牙显出的调皮,让我确定就是她——黄菊英。
有一段时间,黄菊英突然变得沉默,喜欢啃指甲。有时候,文具掉了,我会用手指戳一戳她的背。
她通常转过来,一言不发,只用眼睛询问我。我指指掉在她脚下的文具,她捡起来,反手准确地放在桌子上,不看我。倘若我要说声谢谢,她就摇摇头,然后把指甲递进嘴里,反反复复地啃。啃一阵,会把指甲拿在眼前看看,像是在检验牙齿是否称职。班主任牛法科抽问,她站起来,除了努力往下抻衣角,就是垂着头,一言不发。几次以后,牛老师就不再理她了。
同学们也觉得怪,但没有谁知道原因。有好事者叫我去撬开她的嘴,“谁叫你最喜欢她”。我承认,我那时确实喜欢过她,曾在她的作业本里夹过几次字条,也在她递给我东西时在她指尖上停留一会儿。我这么说,容易让人觉得我是“老司机”。事实上,我在她指尖停留的时间短暂,一切都是没有痕迹却又印痕深深的,那简直让小心脏怦怦直跳。
对她的突然改变,我其实很难过。以前说过的,要一起考上县城一中,到头来不过是我的单手戏。
那一年,似乎注定不平凡。小布什上台,第一个3G 电话经由英国的沃达丰网络拨出,北京申奥成功,“9·11”,加入世贸组织……虽然这些传到小小的县城有了时差,但还带着激荡的余韵,还是能在我们繁重的学习生活中激出些水花。
只不过那些事很遥远,远到似乎可以不管。更切近的水花,是黄菊英激出的。
起因是,一段时间班里频繁地丢东西。一块手表,几块零钱,一个MP3,一个游戏机……牛老师先是在班级恐吓,说已经知道是谁,但为了给他一个机会,请自己承认。这一招显然不奏效,又召开班级干部会议,要大家“暗中盯梢”“检举揭发”。班里安静了一段时间,风头一过,盗贼又出现了。那一次,竟偷到了我头上。我爸从上海出差带回一支英雄牌钢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哪知,在桌子上只待了两天,就不在了。在与不在,只差一个课间。牛老师把大家堵在教室,派我去搜查。我照例搜查了黄菊英的书包,没有,放回去时,正要离开,我看见她裤包里冒出了一截笔帽。我本可以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在回家的路上再叫她还给我,但当初,我可兴奋了,把手伸向她裤包,惊得她恍如遇到了色狼。
我举着钢笔,向牛老师宣布,就是它,就是它,说完,我又向全班看一眼,得勝似的,我看见班级里同样兴奋的神色,从一个中心向教室的四周铺展。
牛老师走下讲台,用书脊砸在黄菊英的头上,“咚”,一声闷响,黄菊英头低了一下,本能地举起手要护住头顶。但牛老师并没给她机会,他一耳光扇过去,黄菊英毫无防备,啪——我似乎听到飞机的音爆,黄菊英的脑袋差点儿给打飞了,身子一转,把书桌撞得“哐当”一声。我惊惶地缩了一下身子,好像那耳光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没偷。黄菊英怯生生地说,声音小得像那年头父亲剃须刀的转动声。
还狡辩,还狡辩。牛老师又扇了她两耳光。桌上的书落了一地,黄菊英扎好的头发被打散了,人比书狼狈。牛老师牵着她一只耳朵,拉到了黑板旁的一个角落,让她站着。
贼,估计一家都是贼,我教书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女贼。牛老师双手撑在讲桌上,不时地飞黄菊英一眼。要是在今天,他会“时髦”地用上“真是活久见”。
我不是偷。没错,是黄菊英,她的声音从披散的头发里挤出来,已经疲弱不堪,以至于牛老师愣了一下,不确信自己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我原来觉得女生都是要脸的,哪个晓得居然有不要脸的。你自己不要脸就算了,莫来祸害班级,也莫来祸害我。我每天事多,没时间陪你耍。要成街妹儿,你就从学校滚出去。估计是家里穷慌了,真是穷蛮,你就说一声嘛,我组织全班同学给你捐,捐钱捐书捐衣服,都得行……
牛老师骂了整整一节课,我们双手交叠在桌子上,腰背打得笔直,盯着他,眼睛不敢稍微转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