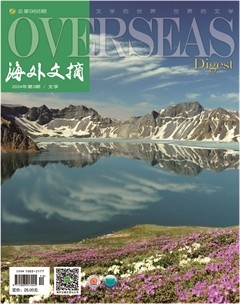深夜,两串脚印从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索利河上越境,向S 国延伸。第三天的黎明前,又有三串脚印越境而去。相距不到二里。
天刚放亮,驻靖宁边防警备巡逻队从边境线走来,厚重的毡疙瘩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惊飞一只七彩山鸡。这帮人的衣领、帽子和眉毛上都挂满了霜花,口鼻喷着白雾。
当少尉发现三串脚印时,立即停下了脚步,看着足迹发呆。不一会儿,他转身望向境内的山林,又往索利河上瞧了瞧,脚印曲折远去。少尉心想,这段界河还不到五里,怎么会在三天之内有这么多人越境?他告诉身后的一个士兵,去把小胡子指导官叫来,有情况不报,非得挨抽不可。士兵走后,天空洋洋洒洒地飘起了雪花。
天大亮时,日军小胡子带着翻译来了,冻得巡逻兵们在雪地上直跺脚。小胡子来到脚印旁,摘下皮手套,用手轻轻地拂去新落的雪,又摸了摸雪印的硬度,诧异地端详起脚尖蹚雪的痕迹,像欣赏工笔画般的仔细。小胡子慢慢地站起身,阴沉着脸,把手套在另一只手上狠狠地抽了两下,骂道,你们这帮蠢猪!骂完,他拿起望远镜望了一眼索利河上的脚印,又转身望向飘雪的山林,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转身走了。小胡子离开后,少尉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脸,没挨耳光,像是捡了大便宜似的。
雪下个不停,绵绵絮絮,挂满枝头,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老赵头抬头望了一眼天空,身背睡袋,大步流星,在前面探路;老孙身穿双排扣制服大衣,头戴卷毛灰皮帽,脚穿长筒靴紧随其后;四炮背着行囊,身着狍皮猎装,脚穿毡疙瘩断后,很警惕的样子。
这三人,老赵头高大、腿长、跑得快,表情木讷,一副深沉的样子。老孙白净、稳重、腰板直,表情威仪,一看就是讲武堂出身。四炮跛脚、脸黑、重胡须,像个门神,因枪法极准,人送外号四炮。老孙初见老赵头时还在纳闷,他才四十出头,怎么会叫老赵头呢?可能是他的化名。
三人越境后,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山路。老孙有些体力不支,脚步踉跄,怀表链在胸前一荡一荡的。他一会儿掏出一块巧克力塞进嘴里,一会儿又掏出洋烟抽一支。老赵头怕暴露行踪,回头将包巧克力的锡纸和烟蒂捡起来,揣进兜里。
雪还在下着,迎风前行,雪花糊在睫毛上,不一会儿便结成了冰晶。走了不知多久,老赵头望了一眼西山,此时天色将晚,便奔向猎人的拍子房(猎人下木拍子的临时住所)。山里人都懂,拍子房里有火种和少量的粮食,不管是谁,只要经过这里都可以享用,以后有机会再给人家补上或扔几个钱。
走进拍子房,老赵头搂了三泥盆雪倒进锅里,又拿起灶台上的火镰、火石和棉花引火。火镰与火石磨擦得火星四溅,也没把棉花点燃。这时,老孙从兜里掏出洋火递给了他。老赵头点燃了茅草,把干树枝放在上面,用嘴使劲儿吹了几口,灶坑里的火苗燃了起来。不一会儿,铁锅里的雪化了,冒着热气,拍子房里有了暖意。
老赵头抬头望了一眼房梁,发现吊着一个面袋子,里面的粮食不多。解下来将玉米面倒进锅里,又从腰间掏出一颗大粒盐放了进去。在扎袋口时,老赵头还夹了一枚北州币。锅里的玉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释放出诱人的香气。四炮看了老赵头一眼,说干柴不多了,趁着天没黑透,我再去捡些回来。老赵头没吱声,只是轻瞟了他一眼。
玉米粥熬好后,老赵头让老孙先吃。可老孙端起粥碗只喝了一口就不再吃了,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大列巴,掰给老赵头一块,自己吃一块。老赵头摇头不要。
不到半个时辰,四炮抱着干树枝走了进来。吃饭时,四炮从怀里掏出一根鹿肉干放进灶坑里,待肉干烤软了,用嘴吹去柴灰,掰成三段,分给了老赵头和老孙。老赵头摆手没接。四炮在吃肉干时,狼吞虎咽,而老孙接过肉干放进嘴里,和着唾液细嚼慢咽,喉结不停地滚动。
吃饱后,倦意潮水般袭来,老孙和四炮躺在火炕上沉沉睡去。老赵头哈腰出门望了一阵风,回来也睡了。不知睡了多久,老赵头做了一个梦,有头黑熊正在追赶他,他越跑越累,两腿像灌铅似的。正当黑熊要将他扑倒时,他猛地醒来,嗓子眼儿干得直冒烟。老赵头坐起来,用手捋了捋喉咙,准备到外面吃点雪,以缓解嗓子的干涩。当他推门来到屋外时,这才发现天空晴了,已是繁星满天。寒风吹过树梢,发出阴森的声响。老赵头哈腰捧起一把雪刚塞进嘴里,发现二里外的沟塘有手电光晃动,时明时暗,若隐若现。老赵头心里“咯噔”一下,不好,小鬼子摸上来了。他没有犹豫,立即进屋把老孙和四炮拽了起来,示意他们拿起东西快跑。三个人背起行囊向山梁跑去,一口气跑出十多里才放慢脚步。
老孙问老赵头,咱们跑了这么远,是不是该歇歇脚了?见老赵头没吱声,四炮也说,长官累得都吃不消了,还是歇歇吧。老赵头还是不出声,继续往前走。天亮后,他们在山里又转了一天,直到天色昏暗。
三人走到一处悬崖下,因这里避风积雪,老赵头才停下了脚步。四炮看了一眼厚厚的积雪,从睡袋里抽出一把短把铁锹,在厚雪处掏出一个雪屋。老赵头去了森林,寻找被大风摇落的干树枝,准备引火。他还顺便把三人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用松枝扫平。在扫雪时,老赵头猛然发现有一双鞋印是正方向的,还有些跛脚。老赵头后背瞬间冷汗沁出。他抱着干树枝回到雪屋,伸手向老孙要了洋火把篝火点燃。引火时,老赵头不经意地窥了一眼四炮的鞋,发现套在毡疙瘩上的反向鞋底不见了。
篝火把雪屋烘得很暖,老孙又把大列巴掏了出来,分别掰给老赵头和四炮各一块。老赵头摆手不要,而是从腰间解下一条灰色头巾,打开后拿出半个玉米饼,放在柴火上烤。四炮接过大列巴,几口吞了下去,一副满足的表情。
吃完飯,老孙侧歪在篝火旁想睡一觉。没承想,老赵头拿起铁锹,将雪扬进了篝火里,瞬间烟火四散,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老孙端着肩严肃地说,不让休息你就说一声,这是干什么?老赵头也不言语,拿起睡袋钻出雪屋,一声不响地在前面带路。老孙本想再训他一顿,可他突然想起在离开S 国时,太平洋秘书处的一位同志告诉他,接你的老赵头,是北州省最有经验的地下交通员,到了国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指挥,这是纪律。想到这儿,他忍了忍,背起挎包跟着老赵头继续前行。四炮也背起睡袋,默默紧随其后。
一路上,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谁也不说话。走夜路时,老赵头每发现一棵弯曲的桦树时,都要停下来观察一下。四炮以为老孙不懂,殷勤地告诉他,冬天刮西北风较多,被大雪压弯的桦树大多朝向东南,可以辨别方向。听到四炮的话,老赵头眉头紧蹙,嘴里厌烦地“咝”了一声,吓得他再也不敢言语了。又走了很长时间,老孙看老赵头还是没有停下的意思,只能继续跟着。从天黑走到天明,又从天明走到傍晚。此时,空中又飘起了雪花,老赵头还在继续走。在路过一个塔头甸子时,老孙不小心摔了一跤,坐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四炮说,老赵头,还是歇一会儿吧,把省委领导累坏了可不好交代。老赵头听后一惊,但仍面无表情。
休息时,老孙掏出最后一块巧克力,掰下一半递给了四炮,自己塞进嘴里半块。四炮含着巧克力,很满足地走到桦树下,解开裤带开始撒尿。老赵头来到他的身后,四炮以为他也要撒尿,也没在意。就在这时,老赵头突然用麻绳勒住了四炮的脖子,一个“小背”,他的双脚已然离地。四炮本能地用一只手去抓麻绳,而另一只手伸向后背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闷响,子弹从背后穿进了自己的身体,双脚挣扎了几下。那个年代,凡是在道上走的都不一般,他们经常把匣子枪倒插在背后布带上,子弹上膛,扳机打开,要是遇到匪徒从背后抱住,伸手就搂火,可保性命。但四炮今天却遇到了对手,老赵头“小背”时,将腰弯下,而四炮被麻绳勒得只能后仰,一枪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四炮抽筋似的动了几下,没气了。
看到眼前的情景,老孙并没有惊慌。他用训斥的口吻说,老赵头,你怎么可以随意处决自己的同志!见老赵头并不理他,又说,看我回到北州省委怎么处分你!
老赵头没吱声,从雪地上扛起四炮的尸体,向沟塘雪深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