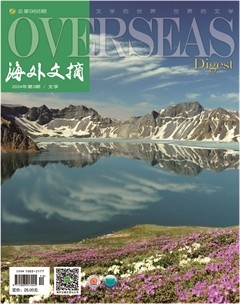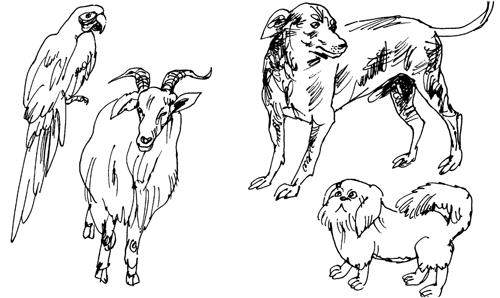
当我说出“Vet”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想倚老卖老。所谓老医生,就是过去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而我这个小兽医,则是现在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当然,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医生过去都和死亡打交道,也不是所有的兽医现在都要同死亡过招儿。但如今我更像一个大人了,知道这样解释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其中确实蕴藏了巨大的力量。我最近和一些自杀的狗狗接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狗狗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快乐是一种伦理道德。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想法,至今依然笃信不疑。或者说,快乐是一种对馈赠的致敬,上帝或者其他什么人,日复一日地赐予我们,突然又在某个时刻撤回的那种馈赠。悲伤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是一种惊奇也是一种必需——但是悲伤必须对快乐俯首帖耳。我的爸爸是个再洗礼派教徒。读中学的时候,我对再洗礼派好好研究了一番,有一个观点打动了我,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正因如此,洗礼的目的与其说是塑造,不如说是追寻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事实也大抵如此。但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我觉得这条经历了五百年风雨的道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选择了再洗礼派,我告诉他追随这个教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说,有点像在寻找已经灭绝的渡渡鸟,不管它多么光彩夺目。他说他记住了我的话,我也相信他记住了。而我已不记得后来是否还和他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我的爸爸,现在已经七十岁了,最近诊断出了慢性白血病。诊断结果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了他的性情。
我爸爸养大了我,全凭他一个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教会了我如何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扎成马尾,他在我来例假的时候带我去买卫生巾,他陪我一起在他的牧羊农场工作。我小时候一直都养狗,有时候养两条,有时候养三条。众所周知,狗狗对于践行快乐这种伦理道德极有天赋。我们的狗,如我爸爸所言,是很好的学习对象。他说得没错。我很难不提及,也很难不投入地讨论关于狗狗的一切细节,我很爱那些狗,但是它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养狗了。我在工作中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死亡。
我成为一名兽医的过程,或者任何需要漫长学习的经历,都是一部从未得到详细记录的启示录。我读书的八年时光,总的来说,就是在教室里目睹快乐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消亡史。这些教室算不上什么糟糕透顶的地方,老师们也不是什么坏人;是我认知有误,觉得这些场景很难让我快乐起来。还有一些我们必须得经由想象完成的动作,看起来愚蠢至极。譬如,我们被告知黑板后面“住了”一个硬纸板做的纸人——纸板模型都放在黑板背后——每次上语法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请”出来,方法就是如同念咒一般呼唤三次他的名字。在下雨的日子里,我们被恩准玩棋盘游戏,比如“对不起!”“超级战舰”什么的,我觉得这两个游戏都太咄咄逼人了。我爸爸经常告诉我,我喜欢以己度人,酿造误解。但他也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之后,到了读高中或者更早的时候,我的同龄人都开始抽条,我也和猫草一样势如破竹地生长,任何新的知识点都让我兴奋,我孜孜不倦地吸入任何需要掌握的知识。我仍然想不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哪种新型的肠道细菌改变了我,或许是那种最常见的、私人定制的上帝伸出了干预之手。在我差不多连续几年都险些“被”留级之后(三年级真的留级了),当我爸爸年复一年被差不多各科老师约谈之后,每个人都开始觉得别的教育方式也许更适合我,所以最后我读了一个兽医学学位,这给了我和爸爸莫大的快乐。但是我知道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毫无出路,因为我们涉渡人生长河的方式就是不断面对意外的起起落落。
周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囫囵吞掉一朵百合的猫咪。我看到了一只把布洛芬连瓶吞进肚子的、足足四十磅重的混血卷毛狮子狗。我看到了一只疑似因为肠扭转呕吐不止的圣伯纳狗。大概到了晚上11 点的时候,一个年纪蛮大的人闯进了急救室,帶着他的公比格犬,他们刚刚遭遇了堵车,比格犬直接就从敞开的车窗里跳了出来;它双侧的肋骨都骨折了。所有的动物都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和悉心照料。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只比格犬是在119 号高速公路阿瑞卡瑞小溪上的桥上,突然从卡车里一跃而下的。比格犬的名字叫作俄亥俄。它的“主人”——这是我们在急救室里常用的称呼,我们也曾开会讨论过是否要换成别的词语,但是“主人”还是被沿用至今,而不是“宠物父母”或者“监护人”什么的——声称,我已经多次说过俄亥俄完全能适应坐在开窗的车子里,之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这个男人,但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个男人。在内心深处,我用马克笔在这个细节旁做了一个记号。我不会撒谎。撒谎是一种病态。但在我知道了其他人有多么依赖撒谎之后,我就在脑海中摊开了一本方格纸笔记本,记下那些没有被证实过的陈述。这对于宠物救助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都会刻意遗漏掉一些重要而不太光彩的细节。
我应该说已经在这个宠物急诊室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但是它最近被一家新公司收购了。所以,一些规矩也变了,并不是所有的新规矩都恰好契合我的价值观。但是,在这里工作终归好过出去自立门户,因为那样你必须完成一大堆客户管理任务,作出设计决定,还要发漂亮的贺卡提醒人们该给宠物打疫苗了,诸如此类的杂事——我肯定会搞砸的。所以,我还是选择亦步亦趋,而并没有深究为什么要这样做,偏偏就是那一天,俄亥俄从车里一跃而下。
我们给俄亥俄做了X 光扫描,将伤口包扎好,它的主人把它带回了家,连同一些止痛药,还有要关注任何感染迹象的温馨提示。
之后,我接诊了一只生命垂危的鹦鹉。我给它做了检查,发现它得了鹦鹉热。我至今仍记得,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的时候,将一只鞋盒递给了一名顾客,鞋盒里面装着一只死去的鹦鹉。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奇怪的规矩。所有的规矩本身就埋藏了奇怪的种子,它们围绕着这颗种子生长起来,也许是要保护、滋养那些奇怪的东西,也许是要将它掩藏起来。
我对鹦鹉的主人解释道——他说自己更喜欢“监护人”这个称呼——他的鹦鹉被检测出了鹦鹉热阳性。我把这些话写在了一张便利签上递给他,因为当面说会让他难以接受。我解释了一下他目前的选择,检测结果极有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接待员凯莉,会开出一张价格昂贵的治疗单。凯莉当时正吃着一根柠檬冰棍,她随即把它平放在餐巾纸上,动手准备相关的书面单据。在兽医的急救室里,每一天上演的悲剧中都会隐藏一些次要情节。
我又开始接待下一位“病人”,一只爪子受伤的赛珠犬。
过了一会儿,我又重新被叫回候诊室。那个鹦鹉的主人告诉我,他已经检索了我和他说的那种病,他的鸟根本没有感染什么衣原体——根本不可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