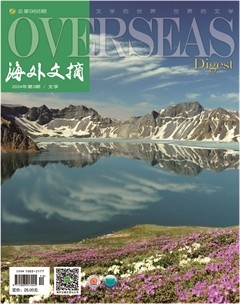一
大表弟來电话,说姨父喘得厉害,在医院住了五天,回家卧床已半个月了,这几天时不时地提起我。他说疫情像一阵风,把全村刮了个遍,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走了好多个。他让我给姨父打个电话,聊聊天。
疫情三年了,一直未能回老家看看,父母坟上的草绿了黄,黄了枯,枯了又生。从哥哥发来的照片看,坟似乎瘦小了许多,心中顿有戚戚焉。
姨父和我们同村,我上中学时,他在县安建公司上班,我每个周末回六十里外的家中带一次干粮,若赶上他也回家时,他便骑自行车驮着我。回家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特别是其中二十多里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姨父个子不到一米七,身体敦敦实实的,骑在自行车上,车座被压得吱扭吱扭叫,他的头一鼓劲儿地往前拱着,背一起一落,哼哼嗯嗯粗重地喘着气,偶尔还发出吹哨一样的哮鸣。我从车后座上跳下来,去抢车把,争着要骑车带他,他坚决不让,两手死死攥着车把,眼睛圆睁,两腮通红,说话都结巴起来:“你、你、你好好坐着,别、别耽误工夫!”就这样,一路无语,风呼呼吹过耳际,姨父的喘息声、车座的吱扭声、车链子咔咔的滚动声混合在一起,姨父的背仿佛着了火,散发出烘热的汗味。姨父一直骑到我家门口,顺手提起我盛干粮的竹筐,把我送回灶屋中,向我妈咧咧嘴一笑,点点头,才返回自个儿的家。
如果姨父不回家时,他周末便在汽车站西面那条公路上给我拦辆搭乘的车。那条路叫张北路,当时是一条繁忙的主干道,轰轰隆隆的拖挂大卡车,车顶上杂乱地摞着五颜六色行李的长途客车,突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的枣红色拖拉机,不知从哪条小路上猛地蹿出来的一辆手扶三轮车,偶尔静静划过的几辆小卧车,路边丁零丁零一摇三摆慢慢腾腾的马车、驴车、牛车,各种车辆像一波又一波的浪头涌过河道,呼呼隆隆驶过马路,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汽笛声、人们的喊叫声、间或响起的高拔昂扬的马嘶驴鸣牛哞混成一团。仔细听时,那马嘶似笑、驴鸣像哭、牛哞如深情呼唤妈妈,让人禁不住愣怔一会儿。姨父塌背含胸地站在马路牙子上,在弥漫的烟尘里,在嘈杂的市声中,两眼紧紧盯着由北往南的汽车。车过了一辆一辆又一辆,他和司机远远地招手,扯着嗓子打问,往往要联系十几辆车,才能让我搭上车。现在想来,那是一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难事。一个人完全和路过的司机不认识,就敢于到公路上拦车搭车,司机竟也可以答应!我猜测,姨父也是有选择地拦车的,比如看那车牌号是我们县的吧,比如司机面相是憨厚慈善的吧,比如那师傅的乡音是老家方向的吧……和司机谈好后,我就被姨父用力托着屁股推到车后厢里。那车有的是拉家具的,车厢里桌子椅子满满当当交叉着摆放,一层层叠上去,高耸得吓人,每当要超车或是拐弯时,我的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双手没抓没挠,身子在桌背和椅腿的缝隙里晃来荡去,不经意间头上便会撞个大包,那包摸上去像一层薄膜包着的一汪水,随时都会从戳破的一个小口迸溅出去。有时搭上的是拉化肥的车,我缩在遮盖的篷布里,刺鼻的气味呛得眼睛生疼,恨不得一直憋住不喘气,衣服上的化肥味儿十几天都散发不了。有时搭的是拉沙子的车,车上滑滑溜溜似乎总在运动的细沙,仿佛随时就要倾泻下去,我双手紧握着,手心里是黏糊糊的汗,两脚痉挛地蜷在灌进细沙的鞋里,就像被铁夹子夹住身子的僵直的鱼。好多年过后,我还会梦见从飞驰的沙车上滑下,从一身冷汗、张开大口却喊不出一丝声音的梦里惊醒。
汽车驶出好远,我透过雾尘,隐隐还看到姨父站在马路牙子上,往这边扬扬手,再扬扬手……
二
姨父是十八岁那年当兵去的甘肃。
那个年代,农村青年想改变土里刨食的命,一是靠升学,二是去当兵。升学,由于取消了通过考试录取的办法,改为群众推荐,普通人家孩子想通过读书到城里工作的路就基本堵死了。能当上兵,便是农村青年的出头之日。
姨父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门心思种地,少与村民打交道,为了独生儿子的前程,他一狠心把养了不到一年的猪卖到公社生猪收购站,硬着头皮往大队干部家跑了好几趟,为姨父争得应征入伍的报名资格。验兵那天,听说前一年村里有个小伙子因为血压高没验过,又听说降血压的秘诀是提前多喝开水。可能是因为心情紧张,姨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担心自己是血压高,出门前咕咚咕咚喝了一暖壶开水。谢天谢地,在紧张不安和热切期盼中,姨父接到了被批准入伍的好消息。
运送新兵的火车是一列闷罐车,每节车厢开着几个小窗,车门离地面足有一米半高,需要攀着一架短小木梯上去。闷罐车里生着炉子,炉子上方悬挂着一盏煤油马灯,散发出昏黄的光,随着火车行进的节奏微微摇动着。车开得很慢,呜呜、咔嚓咔嚓、哐当哐当,姨父心里兴奋得要命,至于他们要去哪里,车程多长,一律不知。白天透过窗子可以望见铺展无际的田野,夜色里一道道山影掠过车窗。跑了三天三夜,火车开进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停了下来。
姨父清清楚楚地记得,到了部队吃第一顿饭时的场景。当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和一箩散发着麦香的大白馒头端上来时,他激动得心都颤抖了,这是梦里也会流口水的伙食啊。大口吞着馒头、喝着菜汤,姨父说那会儿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又想到几千里外的老爹老娘享不到这福分,便增添了愧疚之情,泪水禁不住漫上眼角。“咱以后不好好干,对得起谁啊!”
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从接到入伍通知那天起,姨父就在心底暗暗立下了志向。农村孩子最不怕的是吃苦,最不服的是落伍。姨父说,在新兵连那会儿,每天早晨天不亮,战友们就争先恐后悄没声息地起床去打扫营区的院子。可是只有两把扫帚,如何抢到扫把就成了大家发愁的事。有的战士动了心思,晚上悄悄把扫把藏了起来,第二天早起的战友找不到扫把,急得团团转也没有办法。姨父是个“闷葫芦”,但“闷葫芦”有“闷葫芦”的主意,训练结束,他连续几天到营区周边四处踅摸,想找到扫帚的替代品。山坡上、沟壑里,漫山遍野是高高低低的树木,塔形的油松,尖顶的桧柏,高挺的白蜡,舒展的刺槐,榆叶梅下落满干枯的叶子,忍冬树枝条上晃动着几个扁圆的果子,还有刚刚知道名字的山荞麦、珠芽蓼、马先蒿、火绒草……他尝试着用落在地上的松枝缠上黑麦草扫地,不好用;用柽柳的细长枝条制作,又难以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