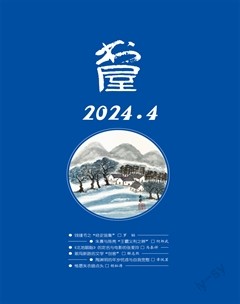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编张旭东先生很推崇广东学人胡文辉,在其新书《藕香零拾》中谈到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时说:“请不要将‘学术史’三个字看得太神圣,我也可以写,你也可以写,只要我们看书和胡文辉一样多、一样细,知道那么多故事,又有很深的学术素养。所以我想北大找个教授,清华再找一个(别找历史系女主任),复旦、中山各找俩,捆在一起,未必就能写得比胡文辉好。当然我的话搁这儿,‘杀猪的’可以驳。”所以,他在关于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的书评《人间幸有未削书》中,谈到罗韬为该书所作的序,他的同事们无不击节赞赏,他自己也直呼“文章真是作手”,但觉得这个“罗韬”寂寂无名,网上也搜不到什么信息,便怀疑是胡文辉化名自作——等闲之辈是写不出如此妙文的。后来,了解到确实是罗韬所作,便觉得像罗韬这样的人,龙潜豹隐,有些传奇。
在我的眼里,罗韬是始于传说,终为传奇。最先知道罗韬这个人似乎是从我导师黄天骥先生那儿。天骥师向来特别关注后学,偶然获读罗韬旧体诗文,赞叹不已,便向一个在《羊城晚报》做领导的学生也即我们的师姐打听,并说“欲得一会其人”,这位师姐自然遵命“组局”。传说“欲求一会”罗韬的,还有政界的好学之士,此公听说罗韬应邀在广州图书馆开讲其新书《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便像学生一般拿了小本本认真在台下听讲。听毕,又像个“忠粉”迎上前去,求加微信。此亦一奇,也堪称岭南文界的传奇。
黄师见过罗韬之后,直言罗韬的学问不亚于其门下高弟。我聆之顿生愧色,也略有疑窦,便时时想见其人,久不可得,而所闻传说更多,其人也更近传奇。比如有《羊城晚报》的朋友告诉我,当年晚报的总编辑微音在报纸上开《街谈巷议》的专栏,每成一稿,必亲呈于罗韬案前,然后立于桌旁,待其改定始肯交付排印。而此际罗韬尚属刚从工人岗位“转岗”的初级编辑。如此光景,洵为传奇。
后来有机会见到那位师姐,她说:“是啊,那时我已经算是采编骨干、中层领导了,但我读到罗韬在外面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以及名家的赞辞之后,我也是自愧弗如啊。”金子终于发光了,罗韬在《羊城晚报》从印刷工人转到财务再到被“收编”,始终沉湎“业务”,不思“进步”,做到报业集团的编委便止步不肯向前。后来,微音的文集出版,序言是请罗韬写的;广东另一位报界大佬杨奇的文集也是请罗韬写序的,这更引发了我对罗韬的一些好奇。同时,我进一步了解到,罗韬进入《羊城晚报》之前,还在广东省台山县中医院做过六年的针灸医生!
相识之后,我还打趣他说:儒者进则仕,退则医,乃宋世以降特别是元代以后的一个优良传统。确实,在从医之前,罗韬的学问文章已经脱颖而出了。方其因为严重偏科(满分一百分的数学只考了二点五分)高考铩羽之际,师友辈便劝其直接报考文史方面的研究生,可是他的严父关键时刻的威嚴,几“误”罗韬终身:“明白了。你考不上本科,就考硕士;如果再考不上硕士,你就考博士——轻佻浮躁!”罗父的“威严”,是出于长期积下的对罗韬专注文史及诸艺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其实也可理解作同情与担忧——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于“从文”的后怕令他们“笃信”理工科的现世安稳。而当他发现罗韬求艺之志终不可阻遏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文化人”的本色——竟安排罗韬从江南到京华,遍访朱屺瞻、陆俨少、许麟庐、钱君匋等名家大师。而“游学”归来,回禀所谓心得,以为年少懵懂,所得不算多,殊不知他父亲以俗语说出最精警之言:“学旧学,就要见下这些旧人,要见下大蛇屙屎。”
确实,这次瞻仰之旅令罗韬受益终身,也堪称罗韬传奇的重要底色来源。前几年,罗韬推出堪称经典的《移花就镜:二十四诗品诗书画印通释》,应该就颇得益于此。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日益专业化的今天,此作能汇通诸艺且自出机杼,得以解决钱锺书先生指出《二十四诗品》所存在的“从抽象到抽象”的问题,实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