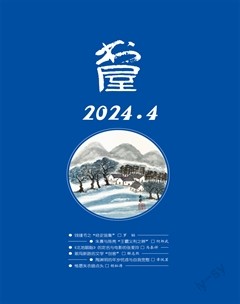一
张爱玲在1955年赴美之后,曾一度尝试继续英文小说的写作,打开英文读书市场,“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言犹在耳,张爱玲此阶段的事业企图心不可谓不大。在她与好友宋淇、邝文美的通信中,张爱玲汇报自己的英文写作进度的文字相当多,其中讨论最后被定名为《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这部英文长篇小说写作细节的内容尤其丰富。
《北地胭脂》脱胎于张爱玲上海时期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进一步将汉语短篇原作改扩为英文长篇小说,并以这个写作计划在1956年申请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部英文长篇小说在1957年完成初稿。在张爱玲书信中,她自己将这部英文长篇小说暂定名《红泪》(Pink Tears),而非通译的《粉泪》。《红泪》在寻求出版的时候却意外受阻,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小说一直在“兜圈子”。到了1960年初,张爱玲沮丧地跟宋淇夫妇汇报“《红泪》至今未卖掉”,直到1967年《红泪》方易名为《北地胭脂》在一家英国出版社出版。在等待出版机会的过程中,张爱玲持续润色这部英文小说,同时开始将其翻译改写回汉语,汉语文本即后来的《怨女》。加上张爱玲自译《金锁记》的英文文本The Golden Cangue,如王德威所言“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由此可见这个故事对于张爱玲的重要性。
无论是哪种文字的版本,小说的篇名张爱玲都曾反复斟酌。汉语文本《怨女》的定名过程让张爱玲非常纠结。定稿前,张爱玲一直以《胭脂泪》称呼这本英译中的小说,又因为“上海气氛很浓,想叫《上海女》”(1965年6月16日信件);后自认“有点鸳蝴气”,“又在考虑叫《错到底》,是一种针脚交错的绣花花样”(1965年8月12日信件),在小说的第二章也出现了女主人公柴银娣以“错到底”花样给鞋面锁边的情节。最后,张爱玲才灵机一动,定名《怨女》,仍旧写信给宋氏夫妇咨询意见,“不知道有没人用过这题目”,可知张爱玲对于作品篇名高度敏感。
同样,英语文本的名字也经历了从Pink Tears到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变化。《金锁记》的题目点明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自虐且虐人,题目自是熨帖;而《北地胭脂》则补充了人物成长经历和爱欲萌动过程,删除了《金锁记》中女儿姜长安一角,着重于女主角柴银娣贪嗔痴欲的离奇一生。篇名乍看之下稍显奇怪,应是由书名《胭脂泪》拓展而来的,但其实也相当合适。小说中一个情节要点是强调柴银娣以“上海本地”的南方人身份,嫁进“烟台姚家”这样南迁上海的北方望族,因此不得不伏低做小遵行家中的“北地规矩”,感受到一种过生活犹如在舞台上“扮戏”一般的苍凉体验。其中姚家女眷的化妆装扮,尤其是胭脂的使用特别具有北地风情:
她曾经注意到他们家比外面女人胭脂搽得多,亲戚里面有些中年女人也搽得猴子屁股似的,她猜是北边规矩,在上海人看来觉得乡气……
…… ……
但是搽这些胭脂还是像唱戏,她觉得他们是一个戏班子,珠翠满头,暴露在日光下,有一种突兀之感;扮着抬阁抬出来,在车马的洪流上航行。她也在演戏,演得很高兴,扮作一个为人尊敬爱护的人。
从《红泪》到《胭脂泪》,再到《北地胭脂》,篇名显然借用了“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的套语。张爱玲曾多次尝试考据“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的典故来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无所获后,写信求助庄信正,“主要想知道是否七世纪写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句子,仍旧查不出”。庄信正不敢怠慢,遍查辞书无果后,又到伯克利请教陈世骧和顾孟余两位先生,结论是大概为“六朝金粉”和“北地胭脂”二词的合凑,仍没有定论。张爱玲也感慨“真想不到这两句话的来历这样复杂”,只得将“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直译为英文作为卷首格言,附加了一句说明,这是“中国形容美人的表述,大约始自七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