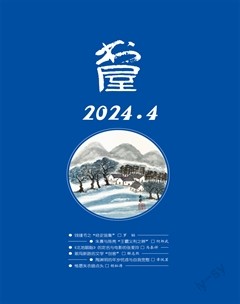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史铁生,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寸步难行,每天盼望着死的时候,同学为了鼓励他激励他,就介绍他认识孙姨,说“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史铁生后来写道:“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因为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的孙姨,中年又相继丧女丧子,而且还戴着“右派”等几顶帽子。
孙姨,就是梅娘。
一
梅娘(1916—2013),本名孙嘉瑞,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于“伪满洲国”(东北沦陷区)的所谓“都城”“新京”(今長春),留学于日本东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华北沦陷区文坛,代表作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和《鱼》《蚌》《蟹》水族三部曲都出版于这一时期。她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女,一度靠做保姆和搬运工维持生计。重新提笔已是1979年,晚年以散文创作为主,著有《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梅娘:怀人与纪事》等。从1936年出版将中学习作选编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小姐集》,到2013年《芳草地》第一期刊载散文《企盼、渴望》,梅娘的写作生涯绵延七十八载。
梅娘作为“出土文物”正式现身,是在钱理群先生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首版的这部文学史第二十八章“在荆棘中潜行的‘孤岛’和沦陷区文学”中提到:
七七事变以后,东北抗日反满文学再度兴起。……同时,围绕《大北新报·大北风》的陈隄、关沫南等作家群,……和围绕《大同报》文艺专页、《文丛》《文选》的山丁、秋萤、袁犀(李克异)、李乔、梅娘、吴瑛等作家群,在表现现实、时代和如何接受祖国文学遗产上,形成不同的文学团体。……东北沦陷区文学是全国抗日文学的前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和鲜明的东北作家个性色彩、地方特点,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认识。
应该说,这个点名录式的粗疏介绍,当年对梅娘而言,可谓云雾渐散曙光乍现。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第1版)中,关于梅娘创作的论述评价就非常具体精准了:
在“雅俗共赏”这一点上与张爱玲小说具有一些共性的,在沦陷区的上海有苏青,在北方的沦陷区又有“南玲北梅”里的梅娘。
…… ……
北方的梅娘(1920— )先后活动于东北和华北。由于她的特殊身世,她的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色。同样是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活遭遇,梅娘的叙述要比张爱玲“俗”,却比苏青“雅”。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三部作品的人物故事虽没有连贯性,在精神气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大家庭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蚌》的梅丽追求个人幸福和自己所爱恋的人,但社会、家庭已经给她设下了无法逃脱的牢笼,她只有等待宰割,就如同蚌肉的命运;《鱼》的女主人公反抗性更进一步,试图用性爱的自由来叛逆无爱的婚姻,但可叹所爱的男人只是个懦夫,她像鱼一样没能钻破渔网;《蟹》的女性结局比前两者光明得多,大户人家出身的孙玲终于离家出走,蟹的行走能力确实要比蚌、鱼都强大。梅娘后来有些短篇如《侏儒》《春到人间》,表现生活的幅度有所扩大,触及人间更多的不平,心理刻画和人性描写都较为深入。梅娘的小说也曾经成为畅销书,仅小说集《鱼》半年时间就印行过八版。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致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此后,不同文学史家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譬如朱栋霖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等,对梅娘及其创作的论述,都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论断为依违。至此,梅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拥有了一席之地。
得知自己进入了文学史,“我终于在我的祖国获得了对我的肯定的评价”,被“汉奸文人”盘押枷锁几十年的梅娘才算真正获得精神解放。2001年3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笔下曾有这样的特写镜头:
关于四十年代的谈话停顿在梅娘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上:“像我这样的文人,采访了做什么?”我心中一愣,岔开了话题,开始谈文学史。我告诉梅娘,我们大学时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一段文字评述了她的创作。老人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她竟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
另外,最新资料表明,梅娘生于1916年农历11月14日。
二
梅娘即“没娘”的谐音。《诗经·小雅·蓼莪》中的“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几乎就是梅娘的人生写照。
梅娘父亲孙志远乃北上闯关东的山东汉子,凭其聪敏、勤谨和毅力,被国民政府驻扎长春的镇守使招为东床快婿,如虎添翼的孙志远日后在中俄边贸中迅速成长为东北一带举足轻重的实业家。他曾从日本购买军火支持进山抗日的马占山;拒绝出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并曾联络军阀计划组织抗日义勇军。